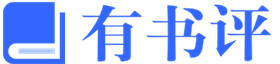贞观二十三年,秋,巳时。
洪福寺的晨钟余音还绕着菩提树,悟空已扛着金箍棒出了山门。老灰说花果山离长安有八百里,若驾筋斗云,半个时辰便能到,可他偏要步行——他想慢慢走,看看这十四年里,大唐的土地到底变了多少,也想再琢磨琢磨唐僧说的“别轻易动武”,到底该怎么做。
路边的稻田里,农夫正弯腰插秧,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,落在泥土里,瞬间就没了踪影。悟空想起当年在车迟国,见过道士把农夫当牛马来使唤,如今这景象,倒让他觉得踏实——至少百姓能安安稳稳种地,不用怕被妖怪或恶官欺负。他走过去,捡起田埂上的水桶,舀满水递给水农夫:“老丈,歇会儿喝口水吧。”
农夫愣了愣,看着悟空毛茸茸的脸,倒没怕,只是笑着接过水桶:“多谢仙长。看仙长这模样,莫不是从西天回来的那位孙大圣?”
“正是俺老孙!”悟空挠了挠头,心里有些得意,“老丈怎么认识俺?”
“长安城里都传遍了,”农夫喝了口水,指着东边,“听说大圣当年在五行山被压了五百年,后来跟着唐僧师父去西天取经,打了不少妖怪。俺们这些种地的,都盼着能有大圣这样的人,帮咱们除害呢。”
悟空心里一暖,又有些羞愧——以前他觉得“除害”就是打妖怪,现在才知道,百姓眼里的“害”,可能是水患,是突厥,是吃不饱饭,这些都不是靠金箍棒能解决的。他拍了拍农夫的肩膀:“老丈放心,俺老孙会帮着师父,让大家都能好好种地,好好过日子。”
告别农夫,悟空继续往东走。走了两个时辰,路过一个小镇,镇口贴着一张告示,上面写着“本镇遭蝗灾,颗粒无收,恳请过往善士接济”。镇子里冷冷清清的,店铺都关着门,偶尔能看见几个面黄肌瘦的百姓,坐在门口晒太阳,眼神里满是绝望。
悟空心里一沉,想起老灰说的“猎人占花果山”,忽然觉得那些猎人说不定也是遭了灾,才来打猎谋生的。他走进镇子,看见一个老妇人坐在门槛上哭,手里拿着一个空碗,碗底还沾着点糠。
“老夫人,你哭啥?”悟空走过去,声音放轻。
老妇人抬起头,看见悟空,眼泪掉得更凶了:“仙长啊,俺家老头子和儿子去山里打猎,好几天没回来了,俺担心他们……这蝗灾闹的,地里没收成,不打猎就没饭吃啊……”
悟空心里咯噔一下,赶紧问:“你儿子是不是二十多岁,拿着一把黑弓?还有你老头子,背有点驼?”
老妇人愣了愣,点头:“是啊!仙长见过他们?”
“没见过,”悟空赶紧掩饰,“俺就是听人说过,山里有猎人。老夫人别担心,他们肯定会平安回来的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两锭银子,递给老妇人,“拿着,去买些吃的,等他们回来。”
老妇人接过银子,对着悟空磕了个头:“多谢仙长!多谢仙长!”
悟空扶她起来,心里更确定了——那些占花果山的猎人,大概率是这镇上遭灾的百姓。他不能一上来就打,得先跟他们说说,花果山是猴子们的家,也得帮他们找条别的活路,不然就算把他们赶走了,他们还是会去别的地方打猎,还是会饿肚子。
一、花果山:棒下留人的悟
悟空走到花果山脚下时,已近黄昏。山门口的几块巨石,当年被他刻上“花果山福地,水帘洞洞天”,如今被猎人凿了几个洞,用来插弓箭。他往上走,听见山里传来猴子的叫声,带着恐惧,还有猎人的呵斥声:“都给我老实点!再叫就杀了你们!”
悟空握紧金箍棒,脚步放轻,悄悄往水帘洞的方向走。水帘洞的瀑布还像当年那样,哗啦啦地流着,可洞口堆着不少猎物的尸体,还有猎人的弓箭和帐篷。几个猎人正坐在洞口喝酒,手里拿着刀,脸上满是疲惫——他们的衣服破破烂烂的,鞋子也磨破了,看起来确实像是遭了灾。
“大哥,咱们这样在山里待着也不是办法,”一个年轻的猎人说,“这猴子越来越少了,再打几天,咱们就没的吃了。”
“那能咋办?”领头的猎人喝了口酒,叹了口气,“镇上遭了蝗灾,地里没收成,去城里要饭都被赶出来,不打猎咱们一家子都得饿死。”
“可听说这花果山是孙大圣的地盘,”另一个猎人小声说,“要是大圣回来了,咱们可就惨了。”
“什么孙大圣?那都是骗小孩的!”领头的猎人哼了一声,“就算他真回来,咱们这么多人,还怕他一个猴子?”
悟空听着,心里的火气又上来了,可他想起老妇人的话,想起唐僧的叮嘱,还是压了下去。他从树上跳下来,落在猎人面前,金箍棒往地上一戳,震得地面都颤了颤:“俺老孙就是花果山的大王,你们占了俺的地盘,杀了俺的猴子,还敢说不怕俺?”
猎人们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,手里的刀和弓箭都对准了悟空。领头的猎人虽然害怕,可还是硬着头皮说:“你……你真是孙大圣?我们也是没办法,镇上遭了蝗灾,没饭吃,才来这里打猎的。”
“没饭吃就能抢别人的家,杀别人的伙伴?”悟空眼睛一瞪,金箍棒又“嗡”地响了一声,“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,也是因为玉帝欺负俺,可后来俺跟着师父取经,才知道不管有啥苦衷,都不能随便伤害别人。”
他指了指水帘洞门口的猎物尸体:“这些猴子,跟你们一样,都是想好好活着。你们杀了它们,跟当年的妖怪有啥区别?”
猎人们低下头,没人说话。年轻的猎人小声说:“大圣,我们知道错了,可我们真的没办法。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,不打猎他们就会饿死。”
悟空叹了口气,收起金箍棒:“俺老孙不杀你们,也不赶你们走。但你们得答应俺,以后不能再杀猴子,也不能占水帘洞。俺会帮你们找条活路,让你们不用打猎也能活下去。”
猎人们愣了一下,随即对着悟空磕了个头:“多谢大圣!多谢大圣!我们以后再也不杀猴子了!”
悟空扶起他们,心里忽然想起当年在狮驼岭,他见了妖怪就杀,后来唐僧跟他说“妖怪也有可怜之处,能度就度”,当时他不懂,现在懂了——所谓“度化”,不是只度化好人,是度化那些走了歪路的人,帮他们回到正途。
他跟着猎人们回了小镇,把镇里的百姓都召集起来,说:“俺老孙知道你们遭了蝗灾,没饭吃。俺会跟长安的师父说,让朝廷拨些粮草过来,再帮你们修水渠,明年种庄稼就不怕蝗灾了。你们要是愿意,也可以去长安的流民安置点,那里有饭吃,还有活干。”
百姓们一听,都高兴得哭了起来,对着悟空磕头:“多谢大圣!多谢大圣!”
老妇人拉着悟空的手,激动地说:“仙长,俺儿子和老头子回来了,他们说再也不打猎了,要跟着您去长安干活。”
悟空笑了,心里忽然觉得,金箍棒不是用来打杀的,是用来保护的——保护猴子,保护百姓,保护所有想好好活着的生命。他想起唐僧说的“济世的经”,现在才真正明白,这“经”就是帮百姓解决吃饭的问题,帮走歪路的人回到正途,帮所有有苦衷的人找到希望。
当晚,悟空在小镇住了下来。他帮百姓修补破损的房子,教孩子们耍棍子(当然是没杀伤力的木棍),还跟猎人们一起商量明年种什么庄稼。夜深了,他坐在屋顶上,看着天上的月亮,心里盘算着:等把小镇的事安排好,就回长安跟师父汇合,然后一起重走取经路。他要跟师父说,他找到自己的“念想”了——不是当齐天大圣,是当一个能帮百姓、能护伙伴的“孙悟空”。
二、高老庄:米香里的坦诚
八戒在高老庄住了三天,每天都帮翠兰干活——劈柴、挑水、种地,把高家的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村民们一开始还怕他,见他每天都勤勤恳恳,也渐渐跟他熟了,有人还会送些蔬菜过来,说“八戒,累了就歇会儿,别累着”。
这天早晨,八戒起得很早,想去镇上买些糯米,给翠兰做糯米糕——他记得翠兰喜欢吃,可他只会吃,不会做,昨天跟村里的王大娘学了半天,才勉强学会揉面。
“八戒,你去哪?”翠兰从屋里出来,手里拿着一件新缝的衣服,“俺给你做了件衣服,你试试合不合身。”
八戒接过衣服,心里暖暖的。衣服是蓝色的,针脚很细,上面还绣了一朵小莲花——翠兰说,莲花是干净的象征,她希望八戒以后都能干干净净做人。他赶紧穿上,不大不小正合适:“翠兰,你手真巧,俺穿着真舒服。”
翠兰笑了,眼角的细纹都舒展开了:“你喜欢就好。你要去镇上买糯米?俺跟你一起去,顺便买些布料,给你再做件冬天穿的棉衣。”
两人一起往镇上走,路上的村民见了,都笑着打招呼:“翠兰,八戒,去镇上啊?”
翠兰点头笑了笑,八戒也拱了拱手:“是啊,去买些糯米,给翠兰做糯米糕。”
走到镇口时,忽然听见有人喊:“翠兰!”
两人回头一看,是个穿着绸缎衣服的男人,骑着一匹白马,后面跟着两个仆人,看起来像是个有钱人。男人看见八戒,皱了皱眉:“翠兰,这是谁啊?怎么跟你一起走?”
翠兰脸色沉了下来:“张公子,这是俺男人,八戒。俺们要去镇上,你有事吗?”
张公子是镇上张员外的儿子,当年八戒走后,他来高家说过亲,被翠兰拒绝了。他上下打量着八戒,嘴角露出不屑的笑:“你男人?就是当年那个抢亲的妖怪?翠兰,你怎么找了这么个男人?又丑又没本事,还不如跟我,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”
八戒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,攥紧了拳头,想揍张公子一顿,可他想起唐僧说的“别轻易动怒”,想起翠兰希望他踏实做人,还是忍住了。他走到翠兰身边,把她护在身后,看着张公子:“俺老孙……俺老猪虽然丑,可俺对翠兰好,俺会帮她干活,会让她开心。你虽然有钱,可你心里只有自己,你配不上翠兰。”
张公子愣了一下,没想到八戒会这么说。他想发火,可看见八戒手里的九齿钉耙,又不敢了——他听说过,八戒是从西天回来的仙长,会降妖除魔,他惹不起。他哼了一声,骑着马走了:“翠兰,你早晚后悔!”
翠兰看着张公子的背影,叹了口气:“八戒,对不起,让你受委屈了。”
“俺不委屈,”八戒摇了摇头,拉着翠兰的手,“翠兰,俺知道俺以前不好,是个妖怪,还抢过你。可俺跟着师父去西天取经,走了十四年,俺学会了做人,学会了踏实干活,学会了疼人。俺虽然没张公子有钱,可俺会用一辈子对您好,不会让您受一点委屈。”
翠兰的眼泪掉了下来,却笑着说:“俺知道,俺一直都知道。当年你走的时候,俺就跟自己说,你不是坏人,你只是鲁莽,你一定会回来的。现在你回来了,俺啥都不怕了。”
两人走到镇上的米铺,买了糯米,又去布料铺买了布料。回去的路上,翠兰忽然问:“八戒,你跟师父说,要重走取经路,是不是还要走十四年啊?俺……俺怕你又走那么久。”
八戒停下脚步,认真地看着翠兰:“翠兰,俺跟你说实话,俺也不知道这趟路要走多久。可俺想带着你一起去,让你看看俺当年走过的路,看看俺是怎么跟师父、大师兄、沙师弟一起打妖怪、取真经的。等这趟路走完了,俺就跟你回高老庄,咱们好好过日子,再也不分开了。”
翠兰看着八戒的眼睛,里面满是真诚,没有一点隐瞒。她点了点头:“好,俺跟你一起去。俺也想看看西天的风景,看看你说的五行山、流沙河,看看你那些师兄弟。”
回到高老庄,八戒就去厨房做糯米糕。他按照王大娘教的方法,把糯米泡软,蒸熟,然后加入白糖和桂花,揉成糕状,再放进蒸笼里蒸。可他手笨,揉面的时候把面粉撒了一地,蒸的时候又忘了看时间,把糯米糕蒸糊了。
“俺咋这么笨呢!”八戒看着黑乎乎的糯米糕,心里很失落。
翠兰走进厨房,看见他的样子,忍不住笑了:“没关系,第一次做都这样。俺教你,咱们再做一次。”
翠兰从新泡了糯米,手把手教八戒揉面,教他怎么掌握火候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落在两人身上,暖暖的。八戒看着翠兰认真的样子,心里忽然觉得,这就是他想要的日子——有翠兰在身边,有糯米糕的香味,有踏实的活干,比当“净坛使者”还开心。
傍晚的时候,糯米糕终于做好了。虽然不如翠兰当年做的好看,可味道却很香甜。两人坐在院子里,一起吃着糯米糕,看着天上的晚霞,都没说话,可心里却满是幸福。
沙僧坐在旁边,看着他们,脸上露出了浅淡的笑。他想起昨天去村里的李大爷家帮忙挑水,李大爷说“沙僧啊,你真是个好人,不像当年那个在流沙河吃人的妖怪”。他当时心里很愧疚,可李大爷又说“过去的事就别想了,现在你帮咱们干活,就是好人”。现在他明白了,所谓“赎罪”,不是靠念经,是靠实实在在的行动,是靠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真心。
“二师兄,三师兄,”一个小猴子从墙外跳进来,是悟空派来的,“大师兄让俺告诉你们,他在花果山帮百姓解决了蝗灾的事,过几天就回长安,让你们也尽快回洪福寺,准备重走取经路。”
八戒和翠兰对视一眼,都点了点头。八戒说:“俺们明天就回长安,跟师父汇合。”
沙僧也点头:“好,俺跟你们一起走。”
当晚,翠兰收拾了行李,把自己的衣服和给八戒做的棉衣都装了进去,还带了些糯米,说“路上给师父和大师兄做糯米糕吃”。八戒看着她忙碌的样子,心里暖暖的——他终于有了“家”,有了愿意跟他一起走接下来的路的人。
三、长安:经卷外的民生
唐僧在洪福寺忙了三天,译经院的事终于有了眉目。他从各州府找来了二十个精通梵文的僧人,还请了长安最有名的学者,一起商议真经的译法。可今天早晨,户部的官员却来告诉她,朝廷拨给流民安置点的粮草少了一半,说是突厥又扰了云州,粮草要优先供应军队。
“大人,流民安置点有三百多个百姓,其中还有不少老人和孩子,要是粮草少了一半,他们会饿肚子的。”唐僧着急地说。
户部官员叹了口气:“御弟,俺也没办法啊。陛下下了旨,突厥那边情况紧急,粮草必须优先供应军队。您看能不能跟流民说说,让他们先少吃点,等军队那边稳定了,再给他们补回来。”
唐僧皱了皱眉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知道军队重要,可流民也很重要——他们已经遭了灾,要是再饿肚子,说不定会出乱子。他想起真经里的《法华经》有云“众生平等”,军队的士兵是众生,流民也是众生,不能因为军队重要,就不管流民的死活。
“大人,俺有个想法,”唐僧说,“俺可以去长安的富户家里化缘,让他们捐些粮草和银两,先补上流民安置点的缺口。您能不能跟陛下说说,再给流民安置点拨些粮草,就算少点也行,别让百姓饿肚子。”
户部官员点了点头:“好,俺这就去跟陛下说。御弟,你真是个心怀众生的好师父,俺佩服你。”
唐僧送走户部官员,就带着几个小和尚去长安的富户家里化缘。他先去了张员外家——张员外是长安最有钱的富户,家里有良田千亩,商铺几十间。可张员外却很吝啬,见了唐僧,只给了一两银子,还说“御弟啊,不是俺小气,最近生意不好,实在捐不出更多了”。
唐僧看着张员外家里的锦衣玉食,心里很清楚,他不是生意不好,是不愿意捐。可他没说破,只是接过银子,躬身行礼:“多谢员外。这些银子,贫僧会用来给流民买粮食,员外的功德,贫僧会记在心里。”
离开张员外家,唐僧又去了李老爷、王大户等几家富户家里,可他们要么给一点银子,要么干脆闭门不见。唐僧心里有些失落,可他没放弃——他想起当年在西天路上,遇到过很多困难,都挺过来了,现在这点困难,不算什么。
走到一家布庄门口时,布庄的老板忽然跑出来,对着唐僧躬身行礼:“御弟师父,俺是布庄的老板,姓刘。俺听说您在给流民化缘,俺愿意捐一百匹布和五十石粮食,希望能帮到流民。”
唐僧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:“刘老板,多谢您!您的功德,不仅贫僧会记着,流民也会记着。”
刘老板叹了口气:“御弟师父,您别谢俺。俺也是从流民过来的,当年俺家乡遭了灾,是一位僧人给了俺一碗粥,俺才活下来。现在俺有能力了,也该帮衬帮衬别人。”
唐僧心里一暖,忽然觉得,这世间还是好人多。他跟着刘老板去布庄搬布和粮食,刘老板还召集了其他几家商铺的老板,跟他们说了流民的情况,他们也都愿意捐些东西——有的捐粮食,有的捐棉衣,有的捐银两。
回到流民安置点时,已是黄昏。唐僧让小和尚把捐来的东西分发给流民,流民们都激动得哭了起来,对着唐僧磕头:“多谢御弟师父!多谢御弟师父!”
一个老人拉着唐僧的手,哽咽着说:“师父,俺们这些人流离失所,没想到还有人愿意帮俺们。您真是活菩萨啊!”
唐僧扶起老人,轻声说:“老人家,您别这么说。俺只是做了俺该做的事。你们都是大唐的百姓,陛下和朝廷都记着你们,等突厥的事稳定了,朝廷就会帮你们重建家园,让你们都能好好过日子。”
这时,一个小和尚跑过来,递给唐僧一封信:“师父,这是大师兄从花果山寄来的信,说他已经帮百姓解决了蝗灾的事,过几天就回长安。”
唐僧接过信,打开一看,里面写着悟空怎么跟猎人沟通,怎么帮小镇的百姓找活路,怎么教孩子们耍棍子。他笑着点头,心里很欣慰——悟空真的长大了,从当年那个只会打杀的猴子,变成了一个懂“济世”的“斗战胜佛”。
当晚,唐僧坐在禅房里,整理着译经院的资料。窗外的月光洒进来,落在经卷上,泛着淡淡的光。他想起今天化缘时遇到的刘老板,想起流民们感激的眼神,想起悟空在花果山做的事,想起八戒在高老庄的幸福,忽然觉得,他的“内在真经”已经取到了一部分——这“经”不是梵文,是百姓的笑脸,是伙伴的成长,是自己为济世所做的每一件事。
他拿起笔,在经卷的空白处写下:“经不在灵山,在民间;佛不在殿堂,在心中。渡人者,先渡己;济世者,先爱人。”
写完,他放下笔,看向窗外的菩提树。月光下的菩提树,叶子轻轻摇晃,像是在跟他说“你做得对,你的路走对了”。他知道,接下来的重走取经路,会有更多的困难,更多的感悟,可他不怕——因为他有悟空、八戒、沙僧,有翠兰,有所有支持他的百姓,有这份“济世爱人”的初心。
四、归程的脚步,向起点靠近
贞观二十三年,秋,第七天。
悟空从花果山回来了。他骑着老灰找来的白马,手里拿着百姓们送的土特产——有花果山的桃子,有小镇的红枣,还有孩子们画的画。他刚到洪福寺门口,就看见八戒和翠兰、沙僧站在那里等他。
“大师兄!你可回来了!”八戒快步走过去,拍了拍悟空的肩膀,“俺跟翠兰都等你好几天了。”
翠兰也对着悟空躬身行礼:“见过大师兄。”
悟空笑了,挠了挠头:“俺老孙回来晚了,让你们久等了。这位就是二师兄常说的翠兰嫂子吧?果然是个好人。”
翠兰笑了笑,没说话。沙僧接过悟空手里的土特产,说:“大师兄,师父在禅房里整理译经院的资料,知道你要回来,特意让俺们在这里等你。”
四人一起往禅房走,路上,悟空跟他们说了花果山的事——怎么跟猎人沟通,怎么帮小镇的百姓解决蝗灾,怎么教孩子们耍棍子。八戒听得很认真,还时不时问几句:“大师兄,那些猎人真的不杀猴子了?”
“当然!”悟空点头,“俺老孙跟他们说了,只要他们好好过日子,俺就帮他们。现在他们都准备去长安的流民安置点干活,再也不打猎了。”
沙僧也点头:“大师兄做得对,不是所有冲突都靠武力解决,有时候真心比金箍棒更管用。”
走进禅房时,唐僧正在整理经卷。见他们进来,赶紧放下经卷,笑着说:“悟空,你回来了。路上还顺利吗?”
“顺利!”悟空点头,把百姓们送的土特产放在桌子上,“师父,这是花果山的百姓送的,您尝尝。俺跟您说,这次去花果山,俺老孙明白了很多事——以前俺觉得金箍棒是用来打妖怪的,现在俺觉得,金箍棒是用来保护的,保护百姓,保护伙伴,保护所有想好好活着的生命。”
唐僧点了点头,眼里满是欣慰:“悟空,你能明白这些,比取到真经还重要。这就是‘内在的真经’,是你自己悟到的,谁也拿不走。”
八戒也开口:“师父,俺跟翠兰也想好了,等译经院的事安排好,俺们就跟您一起重走取经路。翠兰也想看看俺当年走过的路。”
翠兰点头:“师父,俺会照顾好大家的饮食起居,不会给大家添麻烦。”
唐僧笑了:“好,欢迎翠兰加入我们。有你在,大家的日子会更热闹。”
沙僧也说:“师父,俺也准备好了。俺想回流沙河看看,当年俺在那里吃了九个取经人,俺想给他们立个碑,跟他们说声对不起。俺还想帮流沙河附近的百姓修座桥,让他们不用再怕流沙河的水。”
唐僧看着他们,心里满是温暖。他想起十四年前,他们师徒四人从长安出发,去西天取经,当时的他们,各有各的执念——悟空想自由,八戒想回家,沙僧想赎罪,他想取真经。现在,他们又要从长安出发,重走取经路,可他们的执念已经变了——悟空想保护,八戒想珍惜,沙僧想补偿,他想济世。
“好,”唐僧站起身,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,晨光从外面照进来,洒在他们身上,“译经院的事,俺已经安排好了,让其他僧人负责誊抄翻译。咱们明天就出发,重走取经路,第一站,就去五行山,看看当年悟空被压的地方。”
“好!”四人异口同声地说,眼里满是坚定和期待。
当晚,洪福寺的灯笼亮了一夜。唐僧在整理行李,把真经目录和一些常用的经卷装了进去;悟空在跟金箍棒说话,说“明天咱们就去五行山,看看当年压着俺的地方,你可得好好表现”;八戒在给翠兰讲取经路上的事,讲他怎么跟悟空吵架,怎么被妖怪抓,怎么被师父批评;沙僧在念经,念的是《心经》,念到“心无挂碍,无挂碍故,无有恐怖,远离颠倒梦想”时,他忽然笑了,因为他终于懂了,“心无挂碍”不是忘记过往,是面对过往后,还能保持一颗向善的心。
天快亮的时候,唐僧走到院子里,看着菩提树。晨光已经从东边的天际漫过来,把菩提树的叶子染成了金色。他想起十四年前,他从长安出发时,也是这样的晨光,只是当时的他,心里满是忐忑和期待;现在的他,心里满是坚定和从容。
他知道,接下来的重走取经路,会遇到很多熟悉的地方,很多熟悉的人,很多熟悉的事,可他也知道,这次的路,跟上次不一样——上次是为了取“外在的真经”,这次是为了取“内在的真经”;上次是为了度化世人,这次是为了度化自己;上次是“出发”,这次是“归程即起点”。
他拿起笔,在一张纸上写下:“十四年取经路,取的是纸上真经;往后的路,取的是心中真经。归程不是结束,是新的开始;起点不是原点,是悟后的重生。”
写完,他放下笔,看向禅房的方向。悟空、八戒、翠兰、沙僧已经起来了,正在收拾行李。他们的脸上,都带着期待的笑容,像当年出发时那样,可又比当年多了些成熟和从容。
晨光越来越亮,照亮了洪福寺的院子,照亮了师徒四人的身影,也照亮了他们接下来的路——一条从长安出发,往灵山回,往自己的内心回,往“内在真经”回的路。
他们知道,这条路或许很长,或许很难,或许会有新的迷茫和困惑,可他们不怕——因为他们有彼此,有真心,有“归程即起点”的勇气,有取“心中真经”的决心。
这条路,他们会一起走下去,直到找到属于自己的“圆满”,直到悟透属于自己的“人生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