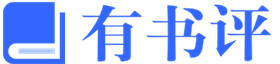南锣鼓巷。
没跑了!
李平安深深吸了口气,那混着陈年老土和人间烟火的气味灌进肺管子。他下意识扯了扯肩上那个干瘪的破包袱(好东西都在空间里躺着呢),抬脚迈进了这条注定跟他纠缠不清的胡同。
冬日的太阳斜照在青灰砖墙上,拉出长长的、冷冰冰的影子。胡同深处,模模糊糊传来小孩闹腾和女人亮堂又带点烦的呵斥声。
下一步,就是在这锣鼓巷的深宅大院里头,把那个传说中的“95号院”给刨出来。给他自己,也给以后要来的妹妹,在这乱哄哄的北平城,寻个落脚的地儿。
他眯了眯眼,逆着光往胡同深处瞅,眼神有点初来乍到的懵,底下却藏着点不显山不露水的劲儿。这卧虎藏龙的四九城,他李平安,来闯了!
巷子不宽,青石板路被踩得溜光。两边院门有开有关,门脸儿高低,透出院里人的穷富。李平安放慢步子,眼珠子跟探照灯似的扫过那些斑驳的门牌号。
95号。
一块乌木门牌,被油烟熏得发乌,边儿都磨圆了,字儿倒还清楚,钉在一扇黑漆掉得露出木头本色的院门边。门墩是俩磨得没样的石鼓,一股子老古董味儿。
就是这儿!李平安心口跳快了一拍,前世那些关于“禽满四合院”的鸡零狗碎、鸡贼算计全涌上来了——号称“三清来了也得扒层皮”的地界儿。他嘴角撇了撇,是真这么邪乎?还是拍戏的瞎编?正好,亲身体验一把。
他装着累得够呛,在95号院门斜对面背风的墙根儿蹲下,破包袱往脚边一撂,眼角的余光却黏在那扇关着的院门上,耳朵支棱着听里头的动静。隐隐约约有锅铲碰锅沿的声儿,还有股子浓烈的、混着油腥和香料的气味飘出来。
吱呀——
院门从里面拉开,一个男人走出来。这人四十上下,个头不高,有点胖乎,裹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棉袄,袖口和前襟蹭着明晃晃的油渍。那眼袋肿得跟俩小水袋似的挂在眼下,透着一股子常年缺觉的蔫巴劲儿。最冲的是那股油烟味,浓得化不开,活像刚从灶台边拔出来。
他手里拎着个空簸箕,像是去倒垃圾,一抬眼就瞧见墙根底下蹲着的李平安。那孩子衣裳破旧,脸黄肌瘦(装的),眼神倒是清亮,不像要饭的,倒像在等人。男人脚下一顿,带着浓重京腔的嗓门儿响起来,透着点纳闷:“小兄弟,杵这儿发愣呢?碰上难处了?等人?”
李平安抬起头,目光跟男人撞个正着。这一看,心里“咯噔”一下!这张脸…这肿眼泡子,这有点刻薄又透着点小精明的五官…活脱脱就是前世那个叫倪大红的演员,年轻了二十岁!一个名字差点从李平安嗓子眼儿蹦出来——何大清!四合院里的厨子,傻柱他爹,后来跟白寡妇拍屁股跑路的那位!
为了探探底,李平安赶紧站起来,脸上挤出点初来乍到的慌和累,嗓子有点哑:“大叔,您好,打扰了。南边逃难来的,路上遭了灾,好不容易才摸到四九城。我叫李平安。”
他指了指95号院门,“听人提过一嘴,说这院里的房主老太太有空房出租?我…我想租两间落脚,不知道…不知道大哥您怎么称呼?”
“哦——逃难来的啊!” 男人明白了,脸上那点打量淡了,多了点街坊邻居式的同情,“我叫何大清,就住这院儿中院正房。你说老太太啊,是有空房。”
他上下扫了李平安几眼,看他年纪不大,又孤零零一个,补了句,“老太太这会儿估摸在家呢,要不…我领你进去问问?”
“何大清!” 名字对上了!李平安心里最后一点嘀咕也散了。果然是禽兽窝!他脸上立马堆起感激的笑,脑袋点得像小鸡啄米:“那可太谢谢何叔了!劳您驾给引个路!”
何大清摆摆手,示意李平安跟上,转身又推开那扇虚掩的院门。李平安深吸一口气,压住心里翻腾的“剧情预告”,把肩上的空包袱紧了紧,抬脚跟了进去,一脚踩进了这传说中“民风淳朴”的95号四合院。
一进院门,光线立马暗了。四合院那四四方方的天井露了出来。青砖铺地,被踩得发亮。正对大门是倒座房,左右两溜是东西厢房,中院两边厢房,正房坐北朝南。后院东西厢房空着。院子不算太大,倒还齐整,角落堆着煤球和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几根晾衣绳横跨天井,搭着些半干的衣裳。
何大清领个陌生半大孩子进来,立马招来院里人的目光。
“大清,这谁家孩子啊?” 何大清媳妇先开了口,嗓门敞亮,带着胡同味儿。
何大清边走边应,声儿不大不小:“南边逃难来的,叫李平安。找老太太看房,想租两间住。”
“哟,租房啊?” 前院西厢房窗户里探出个精瘦的脑袋,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(阎埠贵),“老太太那房可有日子没租出去了。” 话里话外带着点算计。
李平安微微低着头,只当没听见那些议论和打量的目光,紧跟着何大清穿过中院天井,直奔后院。他觉着那些目光像小钩子似的在他身上刮,带着好奇、掂量,没准还有一丝藏着的算计。这院儿里的空气,好像都比外头稠糊。
后院更清净点,正房三间,左右耳房。何大清走到正房门前,抬手在门板上不轻不重敲了三下:“老太太!老太太!我带人来了,看房的!”
屋里传来一个挺清楚、慢悠悠、带着点拿腔拿调的声音:“进来吧。” 听着中气挺足,哪有半点耳背的样儿?
何大清推开房门,一股淡淡的檀香混着旧家具的味儿飘出来。他侧身让李平安进去,自己没往里走,只对李平安说:“小兄弟,你自己跟老太太唠吧,她就住这儿。老太太…咳,你机灵点儿。” 他含糊地带过“耳背”这茬儿,显然门儿清,对屋里扬了扬下巴算是打了招呼,转身就回中院了。
李平安心里明镜似的,抬脚进屋。光线有点暗,缓了缓才看清。屋里摆设老派,但收拾得溜光水滑。一张雕花罗汉床靠墙摆着,铺着深色褥子。一个穿深紫色暗纹绸面棉袄、黑色扎脚棉裤的小脚老太太,盘腿坐在床边小炕桌旁,手里捻着串油光锃亮的佛珠。头发花白,脑后挽着个一丝不乱的小髻,插根素银簪子。
脸上褶子挺深,但皮子白,能看出年轻时的俏模样,一双眼睛不大,却透着一股子经了世事的精明和沉静。五十多岁,腰板挺得倍儿直,浑身上下透着旧式富贵人家那股子拿捏人的劲儿——这就是聋老太太,传说中贝勒府的侧福晋,这会儿眼神清亮,正不动声色地打量李平安。
李平安赶紧上前一步,微微弯了弯腰,声音清楚又恭敬:“老太太您好,打扰您了。我叫李平安,打外地来的,想在您这儿租两间房落脚。”
聋老太太的目光像尺子似的,慢悠悠地从李平安的破衣烂衫量到那个空瘪的包袱,脸上没啥表情,只慢吞吞开口,声儿不高,带着老北京的腔调:“租房?还是…买?” 最后一个字,尾音拖得老长。
“租房,老太太。” 李平安答得干脆,“身上…没那么多钱买。” 他故意挤出点窘迫。
“哦…” 老太太捻佛珠的手没停,“租啊…那得看你看上哪间屋了。价儿…不一样。”
“劳您驾,能带我瞅瞅吗?” 李平安把姿态放得低低的。
聋老太太放下佛珠,慢腾腾挪下罗汉床。她个儿不高,一双小脚走起来倒挺稳当。拿起门边一根乌木拐杖(看着像摆设),带着李平安出了正房。
看房过程挺闷。老太太话少得可怜,只打开门让李平安自己看。后院东西厢房都空着,位置深,光线也暗。中院东西厢房倒是亮堂点,可李平安心里打鼓,觉着中院人多眼杂,是非窝。
最后来到前院,前院东厢房有两间,旁边还带着个小小的耳房。东厢房坐东朝西,下午的太阳正好能斜着照进来,窗棂糊着新换的高丽纸,看着干净亮堂。耳房是小点,但自个儿一疙瘩,当个储藏室或者小厨房正好。关键位置靠前,进出方便,也清静点,正好躲开中院那几位“大神”。
“老太太,这东厢房连带着旁边这小耳房,咋租?” 李平安指着前院东厢房问。
聋老太太拄着拐杖站在院当间,目光扫过那两间房,又落回李平安脸上,慢条斯理地说:“东厢房,一月三块大洋。耳房小,一月两块。先交钱——后住人。” 语气平平淡淡,却带着股子不容商量的劲儿。
五块大洋一个月!眼下这光景,这可不是小钱,够普通人家一个月的嚼谷了。李平安心里反而踏实了。这钱,对他来说九牛一毛,空间里金山银山堆着呢。麻烦的是咋解释一个逃难小子能掏出这钱还不惹人疑心。
他脸上适时地显出点犹豫和肉疼,像是在心里打架,最后咬咬牙,像是豁出去了:“行!老太太,我租了!就按您说的价儿!现在能签契吗?” 他演得像是掏光了家底。
聋老太太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了然,也不多问,点点头:“跟我来吧。”
租房契是现成的格式文书,填上姓名、房号、租期和租金就行。李平安提笔,在承租人那儿写下“李平安”仨字。
写到租金时,他动作自然地解开破棉袄衣襟,从里面一个不起眼的破旧内袋里(实则是从空间里掏),摸出五块沉甸甸、亮闪闪的现大洋,又数出两块当押金(老太太要押二付一),一共七块,轻轻搁桌上。
银元“叮当”一碰,脆生生地响。聋老太太的目光在那几块银元上停了一瞬,伸出枯瘦但干净的手,拿起一块,对着窗户透进来的光,眯眼瞅了瞅成色,又搁嘴边轻轻吹了一下,凑到耳边听了听嗡嗡的余音。
动作老练得很,确认没毛病,她才慢吞吞收起银元,在契约上按了手印,又从一个老旧小匣子里摸出一把黄铜钥匙,递给李平安。
“钥匙收好。房契…得去房管所报备上税,那是我的事儿,不用你跑腿。” 老太太把一份契约递给李平安,“住下吧,院里的规矩…日子长了就明白了。” 最后一句,平平淡淡,却藏着话。
“谢谢老太太!” 李平安接过钥匙和契约,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窝有了,身份的事儿立马又顶上来。他本想顺嘴问问老太太有没有门路办“良民证”,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
这老太太眼神太毒,心思太深,刚来就让她知道自己是“黑户”,等于把把柄递人手里。还是找何大清问问更稳当,那厨子看着市侩,心眼儿估摸没老太太那么深。
他谢过聋老太太,退出了那间飘着檀香和旧时光味儿的正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