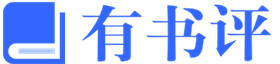简介
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本充满奇幻与冒险的悬疑灵异小说,那么《北舞渡镇》将是你的不二选择。作者“河南孩儿”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关于林河赵清雅的精彩故事。本书目前已经连载,喜欢阅读的你千万不要错过!
北舞渡镇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赶场日的风比往常更硬,像一只看不见的手,翻来覆去地拨弄北舞渡镇的屋檐。
老槐树下,纸灰被风卷成细小的漩涡,绕过茶摊的木腿,贴在地上,又被踏碎。
清早,茶摊的壶先开了。掌柜把茶叶往壶里一撮,滚水一冲,雾气腾地把桌面蒙了一层潮。
两个手背长着老年斑的老人缩在凳子上,对着雾反复叹气。
“我爷爷那辈儿就说,‘舞祖’不是神,是人。”一个说。
“人能镇水?”另一个不服。
“能。穿铃裙,踏七步,吹骨笛。七步里,‘七’不是数,是止——”
“你哪儿听来的?”
“你不也听过么?别装。”
话到这,摊子边围上来几个闲人。说法在嘴与嘴之间拐了几道弯,很快就变了味儿:
——“舞祖是从河上来的鬼新娘。”
——“舞祖是祠堂里选出来的替身,死了才镇得住。”
——“舞祖看谁一眼,谁就会跟着她跳到水里去。”
更离奇的也有:
——“舞祖其实是外乡的先生变的,拿骨笛唬人,收了钱就跑。”
——“舞祖跟‘守笛人’是一对,一个吹,一个舞,不然镇不住。”
每个说话的人都把“我奶奶说”“我外公讲”挂在嘴边。风一来,茶沫在碗里打着转,像是流言也在打着转。
林河提着一小包订好的铁卡,从街心走过,鼻尖全是茶叶与铁锈混合的味。他经过茶摊,听了几句,不由自主慢下了脚。
“你别站这儿。”有人从背后低低唤他。
志远老师绷着脸,手里还夹着摊子上没卖完的两本旧册子。他用眼神示意林河走到拐角。
“别听他们怎么说,先记他们怎么改。”志远压低声音,像在课堂上讲重点,“一个镇子的恐惧,是靠版本滚动起来的。等它滚到你家门口,你就不是听的人,是被说的人。”
“我已经被说了?”林河苦笑。
“你不是,”志远看了他一眼,“她是。”
拐角那端,文化站门口。赵清雅把横幅“北舞渡镇文化站”取下来收好,脸色有些白。门槛前立着两张纸,都是早晨被人悄悄贴上的:“停舞避祸”“勿惹北风”。墨迹还湿着。
老肖在旁边吹胡子瞪眼:“谁贴的!白日里也不遮脸。”一边骂,一边还是把纸轻轻揭下,不敢用力。
“老师。”清雅看见志远,松了口气,“有人说我跳的是‘舞祖步’,会带走小孩……”
志远把那两张纸卷紧,塞进袖子:“你只管记住我昨天说的——七为止,不为进。把‘北’当墙,别去撞。”
清雅点头,目光却忍不住往街心一扫——四面八方的目光像细针,从人群里不由分说地扎过来,让她不适应的不是疼,而是那种被当作“故事里的人”的突兀。
“我带了铁卡。”林河把布包举了举,“门闩我再加一道。”
“好。”清雅挤出一个笑,声音低下来,“今天别多待,晚风怪。”
志远打圆场:“你们都各做各的:你钉卡,她练步。我去学校库房翻抄,看看能不能把‘祭文’的缺字补上两处。”
他说到“祭文”,目光落在清雅腕上的红线,顿了顿,“别向北。”
风从北面拐进来,文化站的窗纸轻轻鼓了一下,又贴回去。
午后,茶摊坐满了嘴勤的人。王三魁扛着刀从街上晃过,草梗堵在嘴角,像一道斜着的钩。他往摊上一坐,笑得慢:“你们都在说‘舞祖’?那我也添两句。”
他把刀背往桌上一拍,语气轻巧:“我听说——舞祖不是一个,是一茬一茬。每回要变天,就选一个丫头,穿铃裙,走七步。走错一步,虚门开;走对七步,水退半尺。”
“哪来的说法?”有人凑趣儿。
“老一辈儿。”王三魁抬下巴,“祠堂里的人知道。可祠堂现在封了,谁知道呢?”
他把话往后一拐,唇角一挑,“**有一点倒不假:舞祖总有个‘心尖儿人’。**那个人,要不一块儿死,要不一辈子活不明白。”
远处的风突然大了一阵,吹得茶碗里的茶面起了一圈圈波纹。
“你说谁?”有人忍不住问。
王三魁“啧”了一声,没点名,却把目光慢慢掠过文化站的方向,像用刀背在空气里划了一道不见痕的口子。
这句话,比“鬼”还像刀。听的人脸上都不自在,笑声变得碎。
流言,找到了名字,下一步就是找脸。
入夜前,志远去了学校库房。库房门锁老,锈得发脆,一拉一合“嘎”的响。他在半层灰里翻出一只掉角的纸箱,里面塞着旧社火照片、节目单、几张拓片。
他把其中一张摊在窗台:黑白照片上是河滩十三石。石前站着一排人,中间一个女孩穿着铃裙,裙摆厚,腰束得很紧。她头发盘起,面容模糊,却能看出眉眼里带着一种硬。照片角落写着两个字:“雨前”。
志远把“雨前”用铅笔圈了两道,又在照片背面匆忙写下:
“流言的骨头是事实,肉是恐惧。
‘雨前’或为仪式启动前的标记。
七步=止步,非进步。
别向北。”
他把照片装进信封,塞进怀里。转身时,门口站着人影。
齐师傅。
“你来借啥?”齐师傅问。
“借记忆。”志远笑,笑意有些疲,“不想再让它只活在嘴上。”
齐师傅“嗯”了一声,把一把旧锁递给他:“别动祠堂。动了,镇不住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志远把锁放回桌上,“我不去祠堂。我去后巷。”
两人对望一息,谁也没再多说。齐师傅转身走了,背影一如往常,像钉在北舞渡的一枚铁。
夜色一层层压下来。文化站的灯泡昏黄,练功房里只有清雅一人。她没跳大段,只把“云手”和“绕花”各走了三遍。每到第七步,她就刻意收,像把心口的乱线一把拢住。
镜子里,她的影子也在收。贴胶的裂缝在灯下像一根被拽紧的弦。她正要关灯,镜底沿又轻轻落下一点灰。
她停住,退半步。
灰停了。
她轻声道:“七为止。”
门外脚步声响,林河来了。
“门闩加好了。”他举举手里的短锤,手背却隐隐发汗,“……我爹今儿到处叫人挖沟,各家都说水要涨。”
“别往北想。”清雅把丝巾收进道具箱,“你回吧。晚上风坏。”
林河“嗯”了一声,犹豫半秒,还是把志远给的那枚黑铁镇纸悄悄递给她:“你拿着,压压心。”
清雅看他,眼睛里像一湾浅水被风吹了一下又平,“你自己呢?”
“我还有你给的那半块糖纸。”他笑,耳尖红,“放枕头底下,也能压一点。”
灯灭。门闩“咔嗒”一声合上。
两人出门,各自朝相反方向走。街心的风把影子剪得参差不齐,像被人用钝刀裁过,边缘都毛了。
后半夜,镇北方向传来第一声闷响,像有人用手掌拍了祠堂的木桌。
有人惊醒,有人没听见。
有孩子在梦里哭了一声,很快被娘的手抚平。
林河坐起,摸到枕下的封套。志远在信笺上写的字在黑暗里几乎会自己发光:“再响第三次时,别向北走。来后巷。”
他把纸压回去。
第二声又来了,重一点,像从地底往上顶。
院墙外,一个极轻极快的脚步停在他家门口,半息又走。
林河穿衣起身,推门到巷子口。风把巷尽头的墙涂成一片潮湿的黑。他看见墙上有一笔粉笔划的记号:一个小小的圆,圆外一撇,指向西。
正与信笺底端的那个小记号一模一样。
他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身后,有人低低喊他名字:“小河——”
他回头,志远从暗处走出,掌心按着胸前的信封,眼里是压不住的急:“别向北。跟我走后巷。”
“现在?”
“第三声快到了。”志远的牙关打着冷,“来的人,也快到了。”
“谁?”
“……该来的人。”
风像被这几个字割裂,变得细细的,冷冷的,贴着墙皮滑过去。
林河没再犹豫,点头。两人贴着墙影,向西而去。
他们路过文化站后墙时,灯已灭,窗纸暗。墙角的地面上,黑铁镇纸反着一点点冷光——像一只压在心上的小石头,替人守着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