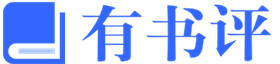红岭乡的晨雾还没被日头彻底驱散,林溪就已经站在了老街的路口。裤脚被露水打湿,紧紧贴在脚踝上,空气中混杂着泥土、青草和远处猪圈飘来的淡淡气味。她胳膊上鲜红的“新菜市场引导组”袖章,被晨风吹得轻轻拍打着手臂。
这是菜市场搬迁攻坚的第三周,也是她和同事们守在路口“劝摊”的第三周。老街的石板路早已坑洼不平,天不亮,各种摊贩就依着几十年来的习惯,将竹筐、扁担、三轮车见缝插针地摆满路面。沾着露水的青菜水灵鲜嫩,土鸡蛋在竹篮里码得整整齐齐。李叔的豆腐摊支在那棵老榕树下,二十多年没挪过窝,见了林溪,总要絮叨:“老街坊都认我这口石磨豆腐,搬走了,味道就不对了嘞!”
林溪趁他低头切豆腐的功夫,悄悄翻开随身携带的速写本,铅笔飞快地勾勒出颤巍巍的豆腐块,还有他沾满豆渣的旧围裙。可老街实在太窄,摊贩一多,立刻水泄不通,赶圩日连三轮车都寸步难行,上个月还差点堵了救护车的路。镇东头新建的菜市场水泥地面平整,排水通畅,棚顶亮堂,可农户们却嘀咕:“离得远,冇人气呦!”(注:冇=没有)
林溪和另外三个年轻干部分成两组,守在通往老街的两个主要路口。见挑着担子的农户过来,她赶紧迎上去,脸上堆着笑,用刚学来的蹩脚客家话夹杂着普通话:“阿婶,今朝的芥菜好靓!新市场头一排嘅好位置同你留到!又亮堂又干净,买菜嘅阿叔阿婶一眼就望见!”遇上犟脾气的老人家,她就挽起袖子,二话不说帮着挑担子,一边走一边算经济账:“阿伯,你睇新市场,落雨唔沾泥,菜摆到都鲜爽几分,一日多卖嘅钱,够割两斤猪肉嘞,好过喺哩度挨挤受累哦!”(注:今朝=今天,靓=好,同=给,留到=留着,睇=看,唔=不,喺=在)
休息的空档,她蹲在路边,翻开速写本,画新市场的轮廓,笔尖划过平整的水泥地,把远处正忙着搬菜筐的农户画成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小黑点。头一周,抱怨和嘟囔不绝于耳,可到了第二周,见新市场里人流渐渐多起来,就开始有农户主动往那边去了。到了第三周,老街路口只剩下零星几个摊位,连李叔的豆腐摊也挪了过去,见了林溪还笑:“还真系要听你们后生仔嘅,新地方系敞亮,买豆腐嘅人都多哩!”
白天的另一项重头戏,是土坯房改造的“一户一档”。她揣着数码相机、厚厚的登记表和新买的卷尺,开始了走村入户的“测绘”工作。王奶奶家的土坯房墙皮脱落得厉害,雨天墙角能接半盆水,是这次改造的重点户。林溪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上阁楼,对着裂缝和朽坏的梁柱拍照,转身又在速写本上记下屋檐的弧度——这些老房子的飞檐,总带着一种历经风霜的温柔。她坐在门槛上,听王奶奶用难懂的土话絮叨:“崽在外头打工,就盼着屋企修企理,过年转来住得安乐啲……”(注:屋企=家,企理=牢固整齐,转来=回来)
每一户的资料都得细之又细。房屋结构照片要拍清承重墙和隐患点,家庭人口、收入情况要反复核对,她生怕漏掉哪个细节,影响了补贴政策的落实。
上周去最偏远的坳背村拍照,摩托车在半路陷进泥潭。林溪把速写本紧紧抱在怀里,和同事深一脚浅一脚扛着设备走了好几里山路。刘大爷家的土坯房藏在竹林后面,木柱子腐朽得能插进手指,她边拍边劝:“大爷,哩只屋真系爱赶紧修哩,唔安全啊。”转身却对着竹林和老屋形成的夹角快速勾勒,笔尖沾了点泥灰,反倒让画面添了几分真实的烟火气。刘大爷搓着手,嘿嘿地笑:“难为你们后生女,比俺自家人还上心。”
日子久了,和村民打交道多了,学客家话成了林溪的“硬任务”。刚来时听村民说话如同听天书,“食饭”(吃饭)、“冇”(没有)、“恁知”(不知道),村干部开会用土话,她全靠同事翻译。后来跟着农户下田,听卖菜阿婆吆喝,速写本上渐渐多了许多拼音加汉字的注脚:“豆角叫‘豆角子’,红薯喊‘番薯’”。前几天在新市场帮张婶算账,张婶指着她速写本上的菜摊笑:“林干部,你画嘅比相片还像!客家话也讲得越来越正哩!”
林溪看着画本里日渐丰满的红岭乡——喧闹的新市场、沉默的土坯房、蜿蜒的田埂、村民的笑脸——忽然觉得,身上沾染的泥土味、资料上散发的油墨香、还有画本里一道道铅笔痕,都成了扎进这片土地的根须,将她与这片曾经陌生的土地,紧密地联结在一起。
傍晚回乡政府时,新菜市场的灯已经亮了起来,收摊的笑语声顺着风隐约传来。办公室里,土坯房改造的资料堆成了小山,她的相机里存着半个乡镇的影像,速写本摊在桌上,最新一页画着灯火通明的新市场,角落写着:“李叔豆腐摊,第三排左二,生意旺得很。”那是红岭乡蓬勃跳动着的脉搏,也是她一步步踩进泥土里,生长出的、实实在在的痕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