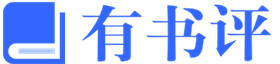半年的加固封印时光,靖安老宅没少出“新状况”。
最先闹起来的是后院那棵老槐树。自从沈青禾的鬼魂消散后,树洞里总传出咿咿呀呀的唱戏声,调子古怪,听得吊哥的绳子都打了结。张一爬上去掏,摸出个褪色的戏服水袖,上面绣着朵半开的梅花——后来才知道,民国时沈青禾总爱坐在树下听戏匣子,这水袖是她不小心勾在枝桠上的,执念竟让布料有了声响。
僵叔倒是得了个便宜。老槐树旁的泥土里翻出个缺角的青花瓷碗,碗底刻着“光绪年制”,他天天捧着当宝贝,说这碗盛过沈大户家的燕窝,比烧烤摊的搪瓷盘“有灵气”。结果某天夜里,碗里凭空多出半碗清水,水面映出个梳着发髻的老太太虚影,瞪着僵叔说:“那是我当年喂猫的碗!”吓得僵叔把碗塞给了白先生——白先生研究半天,说这是“器物留影”,老太太是老宅以前的厨娘,执念全在这碗上。
吊哥也没闲着。他挂着的房梁上不知何时缠了圈红绳,红绳上串着十几个铜钱,风吹过时叮当作响,总把刚睡着的张一吵醒。白先生翻了本《宅经》,说这是“镇梁钱”,民国时盖房必放,能挡煞气,只是年头久了,铜钱里的阳气散了,倒招了些喜欢热闹的小精怪。张一没办法,只好请师父寄来几张“聚阳符”,贴在铜钱上,才算清净些。
最麻烦的是那口枯井。自从阿贞说见过沈青禾的影子后,井里偶尔会渗出些清水,水里飘着碎纸片,拼起来竟是沈青禾日记里没写完的片段:“阿文说,那本书里的字会变,月圆时看,才能见真章……”张一盯着井水犯愁,白先生却蹲在井边摇头晃脑:“水映前尘,井通阴阳,这是老宅在‘说’往事呢。”
某天夜里,血月再现。张一刚把镇魂镜擦得锃亮,就听见井里“咕嘟”冒泡,井水涨得快要漫出来,水面上竟浮着本线装书——正是黑袍人手里那本《阴符经》的残卷。书页自动翻开,原本扭曲的字迹变得工整,末尾还夹着张字条,是阿文的笔迹:“经可辟邪,亦能养邪,心正者用之,心邪者毁之。”
张一恍然大悟,难怪黑袍人用这书招邪,原来关键不在书,在人心。他把残卷拿到老槐树下烧了,火光里飘出个穿中山装的虚影,对着他拱手一笑,转瞬即逝——想来是阿文的执念,见书归正途,终于安心离去。
半年期满那天,师父派人来加固封印,还带来个消息:当年沈大户家的那场火,是厨娘放的。她见沈老爷被黑袍人蛊惑,要拿沈青禾做“血祭”,情急之下点燃了柴房,想烧死黑袍人,却不料火势失控。而那个死在老宅的黑袍人,竟是当年漏网的余孽,潜伏多年想重开“门”,结果栽在了张一手里。
张一收拾行李时,阿贞飘过来,手里捏着片槐树叶:“你走了,谁给我们讲故事啊?”吊哥把绳子缠在他手腕上:“这绳给你,下次遇到麻烦,喊一声我就到。”僵叔塞给他个油纸包,打开是两串烤腰子,还热乎着:“路上垫垫,比你师父给的符管饱。”白先生送了幅字,写着“心正即符”。
张一背着包站在老宅门口,回头看了眼。阳光穿过槐树叶,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,厨娘的猫碗摆在窗台上,吊哥的铜钱在房梁上闪着微光,井水安静地映着蓝天。
他笑了笑,转身离开。手机响了,是师父的短信:“下个案子在南城旧戏楼,有个唱花旦的鬼魂总抢别人的戏服,你去看看。”
张一摸了摸手腕上的红绳,加快了脚步。看来“居委会主任”的活儿,还得继续干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