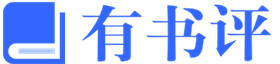南山街道的会议室,第一次挤满了这么多干部。县里新设的“基层治理改革试点小组”在南山落地,表面是“创新”,实则是刀尖上跳舞:整合街道、社区、驻村力量,摸底“街社合一”改革,全市观望,全省关注。
高远挂任街道副主任第二周,就被推到了组长位置。
“年轻,脑子活;还下过乡,上得来、沉得下。”县委组织部的孟副部长亲自拍板。
可真正坐上去,高远才知道,这不是个“锻炼机会”,而是一口没有底的锅。
第一场改革协调会,开在街道三楼会议室。街道科室、社区书记、派出所、城管、民政、卫健、市场监管,十几个部门,全都来人。
刚开始大家还算客气,但不出十分钟,就炸开了锅。
“我们社区才七个正式编,十二个网格要管理,居家养老、低保、计生、疫苗,哪一项不是压死人?你这改革要我们合并报表、整合窗口,是不是根本不考虑基层实际?”
“街道说合一,那我们派出所怎么办?接警、办案、调解、巡逻,你们社区干部能干吗?”
“还有我们市场监管,市局安排我们三天查一次食品店,你这边合一就不查了?”
一个个都在“说理”,可高远知道,说到底,就是怕权力被分、责任被揽。
他一直没说话,直到最后开口:
“我知道大家都不愿动。改革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,肯定有陡坡有硬骨头。我们小组的原则是:不增加一名干部,不撤一项业务,不减一线服务。”
会场顿时安静下来。
他抬手,把提前打印好的《南山试点改革执行方案(草案)》一页页发下去:“我们不是要撤谁、并谁,而是打通信息、合并表格、统一口径、分工协作。谁该出人、谁该定流程、谁该上系统,方案里写得一清二楚。今天我不拍板,只请各位回去逐条看清,下周再来碰头。”
散会后,南山街道党工委书记杜小全拍了拍他肩:“你这是逼他们‘不表态不行啊’。”
高远苦笑:“不逼一逼,永远等不来落地。”
但更大的麻烦,不在会上,而在下面。
第二周,镇西社区有居民举报,说改革组干部“强行干预窗口业务”,把两个服务窗口合并、撤了两名合同工。
“干部瞎指挥、逼人下岗”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县电视台还派人来想采访,街道办一时人心浮动。
“这事不是你干的?”杜书记问他。
“不是我,是个联络员没讲清楚流程,先动了人。”
“但你是负责人。”
高远点点头:“我来处理。”
他连夜写了一份情况说明,按三步解释清楚“试点步骤未执行、联络员擅自行动、社区未通气”的责任划分,主动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,并到镇西社区当面向居民代表解释。
第二天早上,县委组织部发来简讯:高度肯定南山街道“及时回应、实事求是、不遮掩责任”的态度。
第三天,镇西社区一位退休干部在街头巷尾讲:
“这个高副主任,不像那种打官腔的干部。摊上事,没推,也没遮,说得明明白白。”
风评逐渐反转。
真正的暗礁,是来自人事。
改革试点提到“社区服务人员轮岗”,很多合同工心生惶恐,背后开始有风言风语。
“小高是空降的,压根不懂社区,不就是组织部看他会写材料嘛。”
“听说这人之前在山里干过,哪是能干城里事的料?”
“整天跑来跑去,改革搞得人心惶惶,也不怕出事背锅。”
高远一开始忍了。直到有一天,一位社区主任在小组会议上公开质问:
“高主任,如果我们人手调来调去出差错,出了责任谁来担?”
他放下笔,平静地说:“我。”
对方没想到他回答得这么直接,一下没话了。
高远环视众人:“我说过,咱们这项试点,不是哪个单位的试验田,是整个县的‘对标创新’。你们怕被动,我更怕死在台上。所以——谁的任务卡在哪儿,谁的指标完不成,来找我,我来协商、我来跑审批、我来给你们写材料。”
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,有人点头,有人低头,有人依然面无表情。但从那天起,小组的运行明显顺畅许多。
三个月后,《南山街道街社合一改革试点报告》完成,成为全县第一份完整“横到边、纵到底”的试点成果材料。
其中关键章节,多处引用了高远实际操作的案例:如何整合数据口径、如何协调派驻单位共用资源、如何建立“问题清单—协同响应—责任闭环”的流程。
县里召开推广会,书记当众发话:“南山街道这套东西,是干出来的,不是写出来的。”
同事玩笑地拍他:“你小子,这回怕是要火。”
可高远心里知道:这场改革,不是靠聪明完成的,是靠扛。
扛住误解、扛住质疑、扛住没人帮忙的孤独。
他给雷书记发短信:“雷书记,我这三个月才真正知道,山里的累是身体上的,城里累是心里的。可我觉得,我还行。”
雷书记回得简单:“扛得住,才站得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