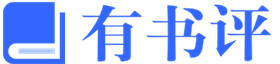喜欢阅读都市高武小说的你,有没有读过这本备受好评的《80平米的岸》?本书以林舟苏萤为主角,展开了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。作者“AI喝点”的文笔流畅且充满想象力,让人沉浸其中。目前这本小说已经连载,最新章节第13章,千万不要错过!主要讲述了:腊月的冻尘裹着寒风敲窗时,小雅已经能准确数出日历上苏萤离开的天数——整整六十天。林舟在厨房煮姜汤,砂锅咕嘟着姜块和红糖的暖香。小姑娘趴在客厅的小桌上,对着苏萤临走前留下的作战靴发呆,靴筒里插着根她捡的…

《80平米的岸》精彩章节试读
腊月的冻尘裹着寒风敲窗时,小雅已经能准确数出日历上苏萤离开的天数——整整六十天。
林舟在厨房煮姜汤,砂锅咕嘟着姜块和红糖的暖香。小姑娘趴在客厅的小桌上,对着苏萤临走前留下的作战靴发呆,靴筒里插着根她捡的野竹枝,是上个月去防护林边缘时折的,现在已经枯成了深黄色。
“林哥哥,苏姐姐说首都的雪会积到膝盖,她的作战靴够暖吗?”小雅忽然抬头,睫毛上沾着点从窗外飘进来的冻尘。
林舟把姜汤倒进搪瓷碗,吹了吹递过去:“她带了咱们缝的暖鞋垫,你塞的那包棉花够厚。”他低头时,看见小雅的笔记本上画满了萤火虫,每只翅膀上都写着“归”字,是她跟着林舟学的新字。
上周社区通报了异兽动向:蚀木虫的尾刺进化出了倒钩,城南的防御带被蛀出三个小孔,猎队连夜修补时,有两只新变异的“冰蚋”顺着裂缝钻进来,翅膀扇动时会凝结白霜,沾到皮肤就像被针戳。
林舟把通报剪下来,贴在苏萤的巡逻记录本里,旁边用红笔标了句“小心低温灼伤”——这是他查遍异兽图鉴续编才找到的应对办法。
夜里写《青崖记》的番外时,林舟总忍不住往苏萤的空椅上瞟。那把椅子上搭着她的米白色毛衣,是临走前洗干净晾在阳台的,现在还带着点阳光晒过的味道。
他在稿子里加了段情节:主角的灵舟在风雪里抛锚,渡口的灯却始终亮着,灯绳上系着片萤火虫翅膀形状的木牌,风吹过时会发出“叮”的轻响。 写到这里,他忽然摸到口袋里的鹅卵石——是苏萤第一次送他的那颗,被体温焐得温热。
三个月的集训期刚过半,苏萤只发来过三次消息,每次都很短:“在学新感知术,能摸到雾蚋的翅振频率了”
“首都的桂花糕不如老城区的甜”
“给小雅买了带铃铛的发卡”。
最后一次消息停在十天前,再没更新。
“林哥哥,苏姐姐会不会忘了我们?”某天夜里,小雅抱着布偶萤火虫钻进他被窝,声音带着哭腔。
林舟把她搂进怀里,闻到她发间的姜汤味——晚上她有点咳嗽,喝了两大碗。“不会的,”他轻轻拍着她的背,“她的作战服内侧还别着你画的全家福呢,比驱逐枪都宝贝。”
这话没说谎。苏萤出发前,小雅把画塞进她作战服内袋,用别针别得牢牢的,说“这样苏姐姐摸感知仪时,就能摸到我们在等她”。
林舟想起那天苏萤弯腰系鞋带时,指尖反复摩挲着内袋的位置,眼眶红得像落了霜的柿子。
冬至那天,林舟带着小雅去老城区的腊梅树旁。雪刚停,枝头的梅花沾着雪,香得清冽。小姑娘踮脚摘了朵,用纸巾包好放进铁盒——那是王队留下的异兽图鉴续编的盒子,现在成了她们的“思念盒”,里面装着苏萤捡的羽毛、小雅画的画,还有林舟写废的手稿。
“等苏姐姐回来,我们把这朵花夹进她的笔记本里。”小雅的鼻尖冻得通红,呼出的白气裹着梅花香,“就像她以前把野竹叶夹给你一样。”
林舟的心忽然一软,蹲下来帮她拂掉围巾上的雪,指尖碰到她冻得冰凉的耳垂——像极了苏萤每次巡逻回来的耳朵。
他想起苏萤临走前的那个清晨,天还没亮,她站在厨房门口看他煮粥,忽然从背后抱住他,下巴抵在他肩上:“集训结束那天,我要吃你做的竹筒饭,放双倍的糯米。”他当时笑着答应,转身时却看见她眼里的不舍,像揉碎的星光。
回到家时,信箱里躺着封首都寄来的信。信封上的字迹有点歪,是苏萤的笔体,邮票上印着首都的防御塔,比他们城的高两倍。
小雅抢着拆开,里面掉出张照片:苏萤穿着新的训练服,站在集训场的雪地里,身后是列队的队员,她的作战服拉链上,萤火虫木牌在雪光里闪着亮。照片背面写着:“新感知术能摸到一百二十米了,等我回来,教你听雾蚋的翅膀声。”
“她没忘!”小雅举着照片在客厅转圈,布偶萤火虫的翅膀蹭到台灯,投下晃动的光斑。林舟摸着照片上苏萤冻红的脸颊,忽然觉得那三个月的等待,像熬一锅慢火的汤,虽然耗时,却把思念炖得越来越浓。
夜里,林舟把照片夹进《青崖记》的番外稿里,刚好在“渡口灯绳”那段旁边。小雅已经睡熟,怀里紧紧抱着那个“思念盒”,嘴角还沾着点下午吃的糖渣。
窗外的防御带蓝光比平时亮些,据说猎队新换了能量板,能挡住冰蚋的低温。 林舟躺在床上,听着隔壁次卧传来的轻微鼾声,手里捏着苏萤送的鹅卵石。
还有三十天,他想。等她回来,要先在门口摆好暖手袋,再把阳台的薄荷挪到窗边,让她一进门就能闻到。 至于那个没说出口的约定——等她回来,就不再分主卧和次卧了。
反正床够大,挤得下两个人的思念,还有小雅偶尔跑来蹭觉的小身子。 窗外的冻尘还在飘,但这80平米的屋里,姜汤的余温、照片的暖意,还有等待的温度,像层厚厚的棉被,裹着所有的牵挂,等那个带着首都风雪气息的人,推门进来。
她还没回来,但归期已近,像雪地里渐亮的天光,越来越清晰。
首都的训练场比十七小队的驻地大十倍,灰色的水泥地上画着密密麻麻的坐标线,像张巨大的棋盘。苏萤趴在战术沙盘旁,指尖沿着新标注的界缝轨迹滑动,作战服的袖口已经被汗水浸得发皱——这是今天第三次模拟感知“冰蚋集群”的动向,新的感知仪屏幕上,淡紫色的波纹比昨天更密集了些。
“苏萤,歇会儿!”赵鹏扔过来瓶水,瓶身上凝着的水珠落在沙盘上,洇出小小的湿痕,“你都盯着沙盘看三小时了,新感知术讲究‘松而不散’,王队以前没教过你?”
苏萤拧开瓶盖喝了口,冰水顺着喉咙滑下去,却压不住太阳穴的突突跳动。她的感知范围已经能稳定在一百二十米,但对冰蚋翅振频率的捕捉总差半秒——那些带着寒气的小异兽,翅尖会分泌冰晶,落在感知仪上像撒了把碎玻璃,干扰判断。
“还差一点。”她把水瓶放在沙盘边,瓶身倒映出战术板上的异兽图谱,冰蚋的翅膀纹路让她忽然想起林舟书里的句子:“最冷的风里,总藏着回家的路。”
夜里躺在集体宿舍的铁架床上,苏萤总习惯摸作战服内侧的口袋。那里别着小雅画的全家福,画纸边缘被体温熨得发卷,王队的徽章硌在肋骨上,像块温热的石头。
她从枕头下摸出林舟给的笔记本,借着走廊透进来的微光写字,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: “Day 45:今天学了‘动态感知法’,能同时追踪五只冰蚋的轨迹了。训练场边缘有片竹林,新叶刚冒尖,想起你蒸的竹筒饭,糯米香混着竹味,比食堂的压缩饼干好吃一百倍。”
写着写着,指尖忽然顿住。笔记本的夹层里掉出片干枯的野竹叶,是去年从城外捡的,被她夹在里面快一年了。叶片上的纹路像条细细的路,顺着脉络能看到尽头——六楼阳台的纱窗,林舟靠在门框上笑,小雅举着糖糕跑,阳光把三个人的影子叠在一起。
集训的强度远超想象。每天清晨五点半,哨声就会刺破黎明,队员们要在负重二十公斤的情况下跑完五公里,接着是四个小时的感知训练,下午还要拆解新式驱逐枪的核心部件。
苏萤的右手虎口磨出了茧,旧伤的左臂在阴雨天会隐隐作痛,但每次拉伸时摸到作战服拉链上的萤火虫木牌,就觉得有股劲从骨头里冒出来。
“苏姐,你总摸那个木牌干嘛?”新队员小李凑过来,他的训练服袖口沾着机油,是下午拆枪时蹭的,“队长说这是‘分心物’,会影响感知精度。”
苏萤把木牌塞进衣领,贴着锁骨的地方暖暖的:“它能帮我找到‘锚点’。”就像林舟说的,无论感知范围多远,心里总得有个稳稳的地方,才能不被混乱的气息带偏。那个锚点,是六楼的灯光,是砂锅里的汤香,是小雅念错“萤”字时的脸红。
周末休息时,队员们结伴去逛首都的集市。苏萤在个卖糖画的摊子前停住脚,摊主正用糖浆画只萤火虫,翅膀上的纹路像极了林舟刻的木牌。
她买了两只,一只递给小李,自己举着另一只慢慢啃,糖渣落在手背上,甜得发腻——像林舟口袋里总装着的橘子糖。
“听说首都的防御带用了新的能量核心,能自动识别异兽进化轨迹。”小李舔着糖画含糊道,“苏姐,你说咱们城啥时候能换上?”
苏萤望着远处的防御塔,塔尖的蓝光比她们城的更亮,却少了点烟火气。“总会的,”她轻声说,“等我们回去。”
夜里写笔记时,苏萤忽然想画灵舟。笔在纸上划了半天,却把灵舟的帆画成了萤火虫的翅膀。
她对着画纸笑了笑,想起林舟写的结局:“灵舟靠岸时,渡口的灯总为归人亮着。”
训练场外的竹林沙沙作响,像有人在耳边说悄悄话。苏萤把笔记本按在胸口,那里的皮肤还留着木牌的温度。还有四十五天,她想。
回去要先给小雅的发卡系上铃铛,再教林舟听冰蚋的翅振声,告诉他:再远的感知范围,都不如家门口那盏灯来得准。
月光透过宿舍的铁窗,在笔记本上投下格子状的影子。
苏萤的指尖划过画错的灵舟帆,忽然觉得,所谓训练,从来不是为了变得更强大,而是为了有足够的力量,守住那些让你想拼命回去的人和事。
就像此刻,她握着笔的手很稳,因为知道,90平米的小屋里,总有人等着她,把思念写成未完待续的篇章。
集训的最后一周,首都的训练场被一层灰雾笼罩。 苏萤站在队列里,作战靴踩着结霜的水泥地,听着扩音器里传来的电流声。
今天是总指挥部的首长亲临训话,灰雾里隐约能看见高台上的黑色身影,肩章在雾中闪着冷光。
“都抬头。”首长的声音透过扩音器炸开,带着金属摩擦般的质感,“你们面前的沙盘,标注着全球十七处活跃界缝的最新坐标。”
他抬手指向沙盘中央的猩红标记,“三天前,北极圈的七号界缝扩张了三倍,出现了‘霜鳞兽’——一种能在零下五十度活动的高阶异兽,尾鳍一挥就能冻结整条防御带的能量管。”
队列里响起细微的抽气声。苏萤的指尖攥紧了感知仪,屏幕上突然跳出血红色的预警线,是模拟器传来的霜鳞兽气息图谱,比冰蚋的寒意在密集十倍,像无数根冰针扎进神经。
“别以为首都的防御带是铜墙铁壁。”首长的声音陡然拔高,“上个月,太平洋的界缝钻出了‘潜沙虫’,它们能啃食海底电缆,现在已经破坏了三座沿海城市的能源中枢。
你们三十支小队来自内陆,或许没见过海水被异兽血染红的样子,但记住——界缝不分海陆,威胁没有边界。”
苏萤的喉结滚了滚。她想起王队生前总说“异兽是跟着界缝走的”,那时她以为只是简单的空间裂缝,此刻才明白,那些撕裂地表的缝隙,像一张遍布全球的网,正一点点收紧。
“这次集训,不只是教你们新感知术。”首长的手指在沙盘上划过,留下一道浅痕,“是要筛选出能‘预判’的人。高阶异兽的进化速度,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数据库更新频率。
上周在亚马逊雨林,发现了会模仿人类电波的‘声纹虫’,它们能伪装成求救信号,诱杀巡逻队。” 赵鹏的呼吸明显变重了。
苏萤侧头时,看见他作战服的袖口在发抖——他的哥哥就是在雨林巡逻时失联的,至今没找到遗体。
“总指挥部决定,组建三十支‘前瞻小队’。”首长的声音终于放缓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,“每支小队配备最新的界缝监测仪,进驻全球最危险的界缝缓冲区。现在给每只小队分配任务,第一小队你们的任务是…十七小队你们小队的任务,是守住华北平原的三号界缝——那里最近监测到‘蚀木虫’与‘沙蠡’的共生迹象,两种异兽正在共享能量源,这是前所未有的进化模式。”
苏萤的心脏猛地一沉。三号界缝,就在他们城市的防御带外侧,是王队守了一辈子的地方。
“下周集训结束,各小队立刻归建。”首长的身影在雾中模糊了些,“给你们三天时间处理私事,然后——”他顿了顿,声音像敲在冰面上的锤,“没有退路。”
解散的哨声响起时,苏萤的感知仪还在发烫。赵鹏走过来拍她的肩,手背上的青筋突突跳:“三天……够回去看一眼吗?” 她望着训练场边缘的竹林,新叶上的霜花正在融化,像眼泪划过叶片。
“够的。”她轻声说,指尖摸到作战服内侧的全家福,画里的六楼阳台,阳光正暖。
当晚,苏萤在笔记本上写了最后一页: “界缝不是裂缝,是活的伤口。我们能做的,不是缝补,是让伤口旁边的人,还能好好吃饭、睡觉、等一个人回家。”
她把笔记本塞进帆布包,又往里面塞了两包首都的桂花糕——小雅说过要比老城区的,还有一支新的感知笔,笔帽上刻着小小的“舟”字。
熄灯前,她最后摸了摸拉链上的萤火虫木牌。还有三天,她想。回去要先抱一抱小雅,再看一眼林舟写的番外,然后告诉他们:这次分开,是为了让所有等待,都有终点。
雾中的训练场安静下来,只有远处的防御塔还在闪着蓝光,像悬在头顶的星。苏萤知道,真正的训练从不是在水泥地上,而是在即将到来的风暴里。
而她的锚点,始终是那80平米的小屋,是炉火上的汤,是等她回家的人。 只是这一次,归期未卜。
集训结束的那天,首都飘起了雨。 苏萤背着帆布包站在车站,雨水打湿了她的训练服,新换的作战靴鞋跟还没磨软,踩在积水里发出“咯吱”的轻响。
赵鹏在旁边清点装备,金属器械的碰撞声混着雨声,像首仓促的离别曲。
“三天后在驻地集合,”他把一把新的驱逐枪塞进苏萤手里,枪身还带着机油味,“队长说这把加装了声波模块,对共生异兽有用。”
苏萤摩挲着冰冷的枪身,忽然想起林舟书里的句子:“武器最该对准的,从来不是威胁本身,是让威胁靠近的缝隙。”
她把枪插进背包侧袋,指尖触到里面的桂花糕盒子,硬纸板已经被雨水浸得发软。 列车驶过三道防御带时,苏萤靠着车窗打盹。
梦里是六楼的阳台,林舟在给薄荷浇水,小雅举着糖画追蝴蝶,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长到能盖住界缝的阴影。
惊醒时,窗外的景色已经熟悉起来——是他们城市的防护林,灰黄色的树干上还留着蚀木虫啃过的痕迹。 推开六楼家门的瞬间,苏萤被一股温热的气息裹住。
林舟系着围裙站在厨房门口,手里还握着锅铲,排骨汤的香味漫了满室。小雅像只小炮弹扑进她怀里,扎羊角辫的发绳蹭到她的下巴,带着股草莓干的甜。“苏姐姐!你看我画的萤火虫!”小姑娘献宝似的递过画纸,上面的三只萤火虫叠在一起,翅膀上写着“家”字。
林舟走过来,自然地接过她的帆布包,指尖擦过她湿漉漉的发梢:“先洗澡,姜汤在锅里温着,放了你喜欢的红糖。”
他的袖口沾着面粉,是下午给小雅做糖包时蹭的,苏萤盯着那点白,忽然觉得眼眶发烫。
洗澡时,苏萤发现浴室的挂钩上多了件新的家居服,浅灰色的,袖口绣着只小小的萤火虫。镜子上贴着张便签,是林舟的字迹:“找裁缝改了袖口,方便你活动胳膊。”
她摸着柔软的布料,想起集训时磨破的训练服,原来有人把她没说出口的疼,都记在了心上。
晚饭时,小雅抱着她的胳膊不肯撒手,叽叽喳喳说个不停:“林哥哥教我写‘界缝’两个字了,他说苏姐姐就是在缝补世界的人”
“楼下张奶奶送了只小猫,叫‘萤萤’,像你的木牌”
“铁皮炉里烤的红薯,我留了最大的给你。”
苏萤一边听,一边往她碗里夹排骨,忽然发现小姑娘的门牙换了新的,比以前更爱笑了。
林舟坐在对面,安静地剥着虾,虾肉都放进苏萤碗里。他没问集训的事,也没提首长的讲话,只是在她喝汤时,轻轻把她的碎发别到耳后:“明天去老城区看看?腊梅应该又开了。”
夜里,苏萤躺在林舟身边,听着他平稳的呼吸。月光透过窗帘缝照进来,落在他的手腕上——那里戴着她编的红绳,串着雾蚋翅膀的地方,被摩挲得发亮。
“三号界缝的事,”她忽然开口,声音轻得像叹息,“我要去缓冲区驻守,可能……很久不能回来。”
林舟的呼吸顿了顿,伸手把她搂进怀里,掌心贴着她后颈的皮肤:“我查过资料,缓冲区的哨所里有灶台,能炖排骨汤。”
他顿了顿,指尖划过她作战服上的新徽章,“我把食谱抄给你,记得放山楂去油。”
苏萤没说话,只是往他怀里钻得更深,像要把这三年的安稳都揉进骨血里。
她想起首长说的“共生异兽”,想起沙盘上猩红的标记,忽然庆幸这三天的短暂相聚——至少能好好抱一抱他,能记住小雅新换的门牙,能把家的味道刻进记忆里,对抗未来所有的风雪。
第二天去老城区时,小雅举着相机跑在前头,给腊梅拍了张照,又给苏萤和林舟拍了张合影。
照片里,苏萤的头靠在林舟肩上,两人的手牵着,背景里防御带的蓝光像条温柔的河。“等苏姐姐回来,我们把照片挂在书架上。”小雅举着相机宣布,小小的身影挡在他们面前,像道小小的屏障。
回家的路上,苏萤在便利店买了两包橘子糖,塞了一包在林舟口袋里:“想我的时候就含一颗,像我在你身边。”
林舟的耳尖红了,从背包里掏出个东西递给她——是个用桃木刻的小盒子,里面放着那片焦羽毛,还有张纸条:“感知到危险时,就摸摸它,我在想你。”
第三天傍晚,苏萤收拾装备时,发现帆布包里多了样东西——是小雅的布偶萤火虫,肚子里塞着片腊梅花瓣。
小姑娘站在门口,眼睛红红的:“它会替我陪着苏姐姐,就像我替你陪着林哥哥。”
林舟送她到驻地时,赵鹏已经带着队员在等了。巡逻车的引擎嗡嗡作响,像头蓄势待发的兽。
苏萤转身抱了抱他,在他耳边轻声说:“别总熬夜写稿,腰侧的疹子还没好利索。”
林舟的手指攥着她的手腕,直到哨声响起才松开,掌心的温度烫得她心口发疼。
“等我。”她说。
“好。”他答。
巡逻车驶离时,苏萤从后窗望出去,看见林舟还站在原地,手里举着那个桃木盒子,像举着整个世界的光。
小雅趴在他肩上,挥着小手,羊角辫在风里飘。 防御带的蓝光越来越近,苏萤摸出布偶萤火虫,花瓣的香气混着硝烟味钻进鼻腔。
她知道,这不是结束,是另一种守护的开始——就像林舟书里写的,“真正的岸,从不是静止的土地,是流动的河,是无论漂多远,都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方向”。
她的方向,始终是那80平米的小屋,是等她归来的人。 而这一次,她要让所有的等待,都值得。
缓冲区的哨所比想象中简陋。
苏萤用石块支起行军锅时,风卷着界缝边缘的沙尘扑过来,锅里的姜汤泛起细密的涟漪。
哨所的铁皮屋顶在风中呜呜作响,像头疲惫的兽,远处的防御带蓝光忽明忽暗,映得沙地上的蚀木虫爬行轨迹像道发光的伤痕。
“苏姐,感知到西北方向有异动。”小李举着监测仪跑过来,屏幕上的绿线与棕线绞成一团——是蚀木虫与沙蠡的共生信号,比训练时模拟的密集三倍,“它们在啃食能量桩的基座,好像在合力打洞。”
苏萤往姜汤里撒了把晒干的山楂,这是林舟塞给她的,说“防胀气,守夜时喝着暖”。
她接过监测仪,指尖划过屏幕上纠缠的线条,忽然想起林舟书里写的“异兽也懂抱团取暖”,只是它们的温暖,是用人类的防线换来的。
“赵鹏带两人去左翼驱逐,”她的声音被风撕得有些碎,“小李跟我去基座加固,带声波驱逐器,频率调到450赫兹——这是它们共生时的薄弱点。”
最后半句,是她熬了三个通宵,在王队的图鉴续编里找到的注解,字迹已经模糊,却透着老队长当年的执拗。
夜里轮岗时,苏萤靠在哨所的墙根嚼压缩饼干。饼干渣掉进衣领,硌得锁骨有点痒,像林舟替她摘头发里的沙粒时的触感。
她摸出帆布包里的桃木盒,打开时闻到淡淡的腊梅香——是小雅塞的花瓣,已经干成了薄脆的黄色,却依然能想起老城区雪后的清冽。
盒底压着林舟的信,是临走前塞给她的,字迹被雨水洇过,有点模糊:“写番外时,给灵舟加了个新功能,能收集界缝的微光导航。你看,再黑的地方,总有能跟着走的光。”
苏萤的指尖划过“微光”两个字,忽然想起集训时首长说的“前瞻小队要做人类的眼睛”,原来所谓前瞻,不过是心里装着要守护的光。
缓冲区的日子在驱逐与监测中循环。苏萤的感知范围又扩展了十米,能在百米外分辨出蚀木虫的爬行声与沙蠡的振翅声,就像能在嘈杂的集市里,准确听出小雅喊“苏姐姐”的调子。
她在巡逻记录本里画满了声波图谱,空白处却总忍不住画只萤火虫,翅膀上标着“六楼”。
林舟的信总是准时寄到,信封上盖着城防邮局的戳,里面夹着小雅的画。最新的一张上,小姑娘画了三个叠在一起的饭团,说“林哥哥教我蒸竹筒饭了,放了野竹叶,等你回来吃”。
林舟在画旁写:“《青崖记》番外写到灵舟穿越界缝,主角把爱人的头发编成导航绳,说‘只要这根绳还在,就不会迷路’。”
苏萤把画贴在哨所的铁皮墙上,旁边是王队的旧徽章。风刮过时,画纸簌簌作响,像有人在耳边轻声说话。
她开始学着在哨所煮竹筒饭,用缓冲区边缘找到的野竹,米是林舟寄来的糯米,蒸到半熟时扔进片腊梅花瓣,香气漫出来时,连监测仪上躁动的波形都平缓了些。
“苏姐,你看这个!”赵鹏举着块蚀木虫的尾刺跑进来,刺尖凝着层沙粒状的结晶,“化验显示是沙蠡的分泌物,能增强腐蚀性。它们真的在共享能量!”
苏萤捏起结晶放在阳光下,折射出诡异的紫光。她忽然想起首长沙盘上的三号界缝标记,像只睁开的眼睛。
“通知各哨位,”她的声音陡然收紧,“把声波驱逐器的功率调到最大,今晚可能有集群冲击。”
入夜时,风里果然传来密集的“沙沙”声。苏萤趴在瞭望塔上,看见沙地上涌动着银灰色的浪潮——蚀木虫的尾刺闪着寒光,沙蠡的翅膀掀起沙尘,两种异兽像条拧在一起的巨绳,正往防御带的能量桩撞去。
“开火!”她扣下声波驱逐器的扳机,高频音波在夜空中炸响,浪潮瞬间乱了阵脚。但下一秒,更密集的异兽从界缝里涌出来,尾刺上的结晶在月光下泛着冷光,像无数把淬了毒的匕首。
激战中,苏萤的作战靴被沙蠡的翅膀扫到,脚踝火辣辣地疼。她摸出桃木盒,指尖触到里面的焦羽毛,忽然想起林舟的话“锚点要稳”。
咬着牙调整感知频率,在混乱的气息里精准锁定共生体的核心——那是蚀木虫与沙蠡连接的部位,比别处的防御弱三成。
“集中火力打核心!”她对着对讲机嘶吼,声波驱逐器的蓝光在她掌心跳动,像只挣扎的萤火虫。
天快亮时,浪潮终于退去。苏萤瘫坐在瞭望塔上,脚踝的伤口渗出血,染红了作战靴。
她摸出林舟寄来的橘子糖,剥开糖纸塞进嘴里,甜味在舌尖漫开时,忽然看见东方的天际泛起鱼肚白,像六楼阳台的晨光。
掏出笔记本写新的一页时,笔尖在纸上抖得厉害:“今天守住了能量桩,像守住了家里的灶台。原来所谓防线,从来不是冰冷的金属,是锅里的姜汤,是信里的画,是知道有人在等你回家的念想。”
远处的界缝还在吐着灰雾,但哨所的行军锅里,新煮的竹筒饭正冒着热气,野竹的清香混着糯米的甜,像条温柔的绳,一头系着界缝边的硝烟,一头拴着六楼的炊烟。
苏萤知道,这只是开始。但只要那80平米的屋里还有人等,她就敢往更深的黑暗里走——因为她的岸,永远在那里,亮着灯,温着汤,等她把所有的风雨,都挡在门外。
小说《80平米的岸》试读结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