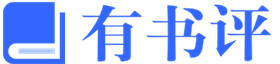简介
喜欢看年代小说,一定不要错过麦冬1234写的一本完结小说《青藤街的暖阳》,目前这本书已更新150140字,这本书的主角是周明远。
青藤街的暖阳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青藤街的清晨总带着股潮湿的凉意,像是浸在深秋的露水里。赵叔推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,慢悠悠地走在石板路上,车铃“哐当哐当”地撞着车把,在寂静的老街上格外响亮。车后座的绿色邮包鼓鼓囊囊的,里面装着今天要送的信件,最底下压着个用牛皮纸包好的长条形物件,是他特意给周明远捎的东西。
“赵哥,早啊!”街角修鞋摊的老王头探出头打招呼,手里还拿着只没修好的皮鞋,“今儿这风够劲儿,您老可得多穿点。”赵叔停下脚步,往冻得发僵的手里哈了口热气:“可不是嘛,这鬼天气,冻得骨头缝都疼。”他指了指邮包,“刚给周老哥送完信,那老伙计看着精神头还行,就是愁容满面的,估计还在为拆迁的事犯愁。”
老王头叹了口气,放下手里的皮鞋:“谁说不是呢?昨儿看见拆迁队的人又在墙上喷字,被街坊们轰走了。那红‘拆’字看着就闹心,好好的老街,说拆就拆了?”他用锥子在鞋底扎了个洞,声音沉了下去,“我这修鞋摊摆了三十年,赵哥您送信跑了四十年,周老哥的杂货铺开了一辈子,这青藤街的一砖一瓦,哪样没藏着咱们的念想?”
赵叔点点头,蹬上自行车继续往前走。车胎碾过石板路的缝隙,发出“咯噔咯噔”的声响,像是在数着青藤街剩下的日子。他今年五十八岁,还有两年就退休了,这邮差的活儿干了整整四十年,从青涩小伙儿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,青藤街的每一户人家、每一棵树、每一块砖,他都熟得像自家后院。
年轻时他骑着崭新的绿色自行车穿街过巷,车铃清脆,笑声爽朗,街坊们听见铃声就知道“小赵”来了。那时候的青藤街热闹得很:街东头的剃头铺总飘着肥皂水的味道,街西头的裁缝店门口挂着五颜六色的布料,周明远的杂货铺里永远挤满了孩子,林慧站在柜台后笑眯眯地给大家分糖果。他送的信也多,家书、情书、汇款单,每一封都藏着说不尽的牵挂。
可现在呢?剃头铺改成了快餐店,裁缝店变成了快递驿站,孩子们都捧着手机玩游戏,谁还会蹲在杂货铺门口等一封远方的信?赵叔摸了摸邮包,里面的信件寥寥无几,大多是些广告和账单,手写的家书几乎绝迹了。他叹了口气,车把上的布包随着车身晃动,里面装着周明远托他找的老邮票,是林慧生前最喜欢的栀子花图案。
到了周明远的杂货铺门口,赵叔支好自行车,看见门口的木板墙上又添了新画。林小满用彩色粉笔画了个举着信件的邮差,虽然画得歪歪扭扭,那顶绿色的帽子和斜挎的邮包却一眼就能认出是他。画中的邮差身边围着几个孩子,手里都举着玻璃珠,在阳光下闪着光,把旁边的红“拆”字遮得严严实实。
“这孩子,有心了。”赵叔笑着摸了摸画中的自己,指尖触到冰凉的墙面,却觉得心里暖暖的。他推开杂货铺的木门,“吱呀”的声响里,周明远正蹲在煤炉边翻找着什么,货架上的玻璃罐里,各色弹珠在晨光中折射出细碎的光斑。
“周老哥,我来啦!”赵叔把自行车推进屋,顺手带上门挡住寒风,“给您捎了好东西。”周明远抬起头,手里拿着本泛黄的相册,眼睛里带着红血丝,像是没睡好:“赵哥来啦,快坐,刚烧的热茶。”他把相册放在柜台上,封面上的“青藤街记忆”几个字已经褪色,边缘处磨得发毛。
赵叔接过热茶,暖手的同时目光落在相册上。翻开的那页贴着张老照片,是二十年前青藤街的集体照,他穿着崭新的邮递员制服站在第一排,身边是抱着周磊的林慧,周明远举着刚修好的闹钟站在后面,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年轻的笑容。“这张照片我还有印象,是那年街道办组织拍的,说要给老街留个念想。”赵叔指着照片里的自己,“你看我那时候,头发多黑,现在都快白完了。”
周明远笑了笑,翻过一页,里面贴着些信件的信封:“这些都是当年街坊们寄来的信,林慧说要留着,等老了慢慢看。”他指着其中一个信封,上面的字迹和苏晓棠的信很像,“这是晓棠丫头寄给林慧的,说她在外地种了棵青藤,盼着它爬满墙。”
赵叔凑近一看,信封上的邮票正是他昨天给周明远找的栀子花图案:“这邮票可是稀罕物,当年发行量少,现在很难找到了。林慧嫂子喜欢栀子花,您每年都在铺子门口种,花香能飘半条街。”他从邮包里拿出牛皮纸包,“给,您要的邮票册,我从家里翻出来的,里面还有几张栀子花的,您看看能用不。”
周明远接过邮票册,手指轻轻摩挲着泛黄的纸页。册子里的邮票按年份排列,从建国初期的老邮票到新世纪的纪念票,每张都用透明纸隔开,旁边还标注着发行日期和背景故事。“你这册子保存得真好。”他翻到栀子花邮票那页,眼眶忽然红了,“林慧走的那年,门口的栀子花都谢了,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了,没想到……”
赵叔拍了拍他的肩膀,没多说什么。他知道周明远和林慧的感情,当年林慧是青藤街小学的老师,温柔又漂亮,多少小伙子惦记着,可她偏偏看上了木讷的周明远。有人说他们不般配,林慧却总笑着说:“明远的心细,能把日子过成诗。”后来周明远开杂货铺,林慧就在旁边摆了张桌子,给孩子们辅导功课,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两人身上,是青藤街最美的风景。
“对了,昨天给您的信,您看出是谁寄的了吧?”赵叔转移话题,不想让气氛太沉重。周明远点点头,从抽屉里拿出苏晓棠的信:“是晓棠丫头,这孩子有心了,十年了还惦记着老街。她说等学成了就回来,给青藤街画图,把老房子都留住。”他指着信末尾的青藤叶,“你看这叶子,还带着香气呢。”
赵叔接过信仔细看着,忽然“咦”了一声:“这邮戳有问题。”他指着信封角落模糊的邮戳,“这不是十年前的,看日期应该是半年前寄的,估计是邮局分检的时候出了差错,混进旧信件堆里了。”周明远愣住了:“你的意思是……晓棠丫头半年前就寄信了?”赵叔点点头:“十有八九是,这丫头说不定已经回来了,或者正在回来的路上。”
这个发现让周明远的眼睛亮了起来,像是黑夜里燃起了火苗。“真的?那她现在在哪儿?”他激动地抓住赵叔的手,指节都有些发白。赵叔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背:“您别急,信上没写地址,但她学的是建筑设计,说不定是回来参与老街改造的。我帮您问问局里的年轻人,现在的孩子都用手机,说不定能查到她的联系方式。”
周明远重重地点头,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他把信小心翼翼地收好,像是捧着稀世珍宝:“要是晓棠能回来就好了,她是个好孩子,懂老街的心思。”他从货架上拿下个铁皮盒,里面装着些旧信件,“这些都是晓棠小时候写的,您看她写的字,多认真。”
赵叔看着那些稚嫩的字迹,忽然想起苏晓棠小时候的样子。那丫头总背着个红色的小书包,跟在他身后问东问西:“赵叔叔,信能寄到天上吗?”“赵叔叔,为什么邮票上的栀子花不香?”“赵叔叔,我能跟您一起送信吗?”他那时候总笑着说:“等你长大了,赵叔叔教你。”没想到这一等,就是十几年。
“周叔,赵爷爷!”门口传来清脆的喊声,林小满背着书包跑进来,脸上沾着粉笔灰,手里举着几颗亮晶晶的玻璃珠,“您看我捡的珠子,里面有星星!”他跑到柜台前,把玻璃珠放在阳光下,珠体里的气泡在光线下流动,真像星星在眨眼。
赵叔笑着接过玻璃珠:“这珠子真好看,比赵爷爷见过的邮票还亮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小小的放大镜,递给林小满,“这个送你,修东西的时候能用得上。”林小满眼睛一亮,接过放大镜就往奥特曼玩偶身上照,看着玩偶身上的针脚在镜片下变大,兴奋地拍手:“能看清了!我能把它修得更好了!”
周明远看着这一幕,转身从里屋拿出个布包,里面是他连夜炒的瓜子:“尝尝,林慧生前最爱炒这个,说冬天嗑瓜子暖和。”赵叔抓了把瓜子,嗑得“咔嚓”响:“还是嫂子炒的瓜子香,有股焦糖味。”他忽然想起什么,从邮包里拿出最后一封信,“对了,这是给李婶的信,她家远房亲戚寄来的,您帮我转交一下。”
周明远接过信,看见信封上的地址是“青藤街38号”,心里忽然一动。李婶的房子就在杂货铺隔壁,是青藤街最老的建筑之一,据说民国时期就有了,院子里那棵石榴树还是李婶嫁过来时栽的,每年夏天都结满红灯笼似的果子。拆迁队早就盯上了那房子,说要作为“重点拆除对象”,李婶为此愁得几夜没合眼。
“李婶最近身体不好,总咳嗽。”周明远把信收好,眉头皱了起来,“昨天还说心口疼,去医院拿了药。我让她搬来跟我住,她不肯,说要守着那房子,等她孙子放假回来。”赵叔叹了口气:“老一辈人都这样,房子就是根,根没了,人就飘了。”他嗑完最后一粒瓜子,把瓜子壳收进纸篓,“我得接着送信了,下午还要去局里整理旧档案,看看能不能找到晓棠丫头的线索。”
周明远送他到门口,看着赵叔蹬着自行车消失在街角,车铃“哐当哐当”的声音越来越远。林小满忽然指着墙上的粉笔画:“周叔,我们把赵爷爷画进去吧!就画他骑着自行车送信,后面跟着好多孩子!”周明远点点头,从屋里拿出彩色粉笔:“好,咱们一起画。”
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墙面上,周明远握着林小满的手,在画纸上添了辆歪歪扭扭的自行车,车后座的邮包上画着大大的栀子花。林小满则在车轮旁画了串玻璃珠,珠子连成长长的线,从街头一直延伸到街尾,像条闪闪发光的项链。“这样赵爷爷送信的时候,就能踩着光走了。”少年仰着小脸说,眼睛里满是认真。
周明远看着墙上渐渐完整的画面,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。他知道拆迁的威胁还在,未来的日子不会轻松,但只要赵叔还在送信,林小满还在画画,街坊们还在守护着老街,青藤街就不会真的消失。那些藏在老物件里的回忆,那些写在信纸上的牵挂,那些嵌在画里的玻璃珠,都会变成老街的根,深深扎在这片土地上。
中午时分,李婶端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走进来,看见墙上的新画,眼睛一亮:“这不是小赵吗?画得真像!”她把粥放在柜台上,指着邮包上的栀子花,“这丫头画的是晓棠吧?跟她小时候一个样,扎着羊角辫,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”周明远把信递给她:“您家亲戚寄来的信,赵哥让我转交的。”
李婶接过信,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着,忽然笑了:“是我侄女寄来的,说她儿子考上大学了,学的也是建筑!跟晓棠丫头一样!”她把信揣进怀里,像是揣着宝贝,“我就说嘛,好人家的孩子都有出息。等晓棠丫头回来,让她给咱老街设计设计,保准比那些开发商弄得好。”
林小满抱着修好的奥特曼玩偶跑过来,举到李婶面前:“李奶奶,您看我修好的奥特曼!它能保护老街!”李婶笑着摸了摸他的头:“好孩子,真能干。以后咱们老街就靠你和晓棠丫头守护了。”她从口袋里掏出块水果糖,塞到林小满手里,“吃块糖,甜甜蜜蜜的,日子就好过了。”
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,周明远坐在柜台后翻看着赵叔送的邮票册,林小满趴在桌上用放大镜研究奥特曼玩偶,李婶坐在煤炉边缝补袜子,杂货铺里弥漫着米粥的香气、煤炉的烟火气和淡淡的樟脑味,温暖又踏实。墙上的挂钟“滴答滴答”地走着,像是在诉说着青藤街的故事,那些关于等待、关于守护、关于温暖的故事。
赵叔骑着自行车走在青藤街的另一端,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路过正在拆除的旧厂房,看着推土机把墙壁推倒,扬起漫天灰尘,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。但当他看到街角墙上孩子们画的画,看到玻璃珠在阳光下闪烁的光,看到周明远杂货铺窗口透出的暖光时,又觉得充满了力量。
他知道自己送的可能是青藤街最后的信件,骑的是最后的二八大杠,守的是最后的老时光。但只要还有人在等信,还有人在盼着远方的消息,还有人记得青藤街的模样,他就会一直送下去,直到骑不动自行车的那天,直到青藤街的最后一缕阳光落下。
傍晚时,赵叔再次路过杂货铺,看见周明远和林小满正在门口挂玻璃珠风铃。几百颗玻璃珠串成的风铃在风中轻轻摇晃,发出“叮咚叮咚”的声响,像无数个小小的音符在唱歌。夕阳的金光透过玻璃珠,在地上投下斑斓的光影,把整个街角都染成了温暖的颜色。
“周老哥,这风铃真好听!”赵叔停下车,抬头看着风铃,眼睛里闪着光,“比邮局的铜铃还响。”周明远笑着说:“等晓棠丫头回来,让她给风铃设计个架子,更结实。”林小满则跑到赵叔身边,举起放大镜给他看:“赵爷爷,您看这珠子里有晚霞!”
赵叔顺着放大镜看去,玻璃珠里映着漫天的晚霞,像把整个天空都装在了里面。他忽然觉得,自己送了一辈子信,送过无数的牵挂和思念,却从未送过这样的风景——青藤街的晚霞,玻璃珠里的光,老人的期盼,孩子的笑容,这些才是最该被留住的东西。
他蹬上自行车往邮局赶,车铃“哐当哐当”的声音在夕阳里格外清脆。他要去整理那些旧档案,要去寻找苏晓棠的消息,要告诉所有人:青藤街还在,这里的暖光还在,这里的故事,还没有结束。
杂货铺的灯光渐渐亮起,温暖的光晕透过窗户,映在墙上的粉笔画上,映在摇曳的玻璃珠风铃上,映在周明远和林小满的笑脸上。远处传来赵叔自行车的铃声,越来越远,却又像是从未离开,在青藤街的暮色里,在每个人的心里,轻轻回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