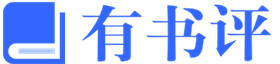一本引人入胜的历史脑洞小说,逆天命:元清明,正在等待着你的发现。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,人物形象栩栩如生,让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奇幻与冒险的世界。作者天涯沦落人001的精湛文笔和细腻描绘,更是为这本小说增添了不少色彩。目前,小说已经连载,最新章节第12章更是让人热血沸腾。快来加入这场阅读盛宴,124308字的精彩内容在等着你!主要讲述了:至正十一年四月廿三,苏州沈府的粮仓地窖里,潮湿的空气里浮着陈米的香气。沈万山用象牙秤称完最后一袋糙米,看着账房先生在竹简上刻下“四月廿三,入库晚稻三千石,水分三成,可存至明年麦熟”,指节在冰凉的秤杆上…

《逆天命:元清明》精彩章节试读
至正十一年四月廿三,苏州沈府的粮仓地窖里,潮湿的空气里浮着陈米的香气。沈万山用象牙秤称完最后一袋糙米,看着账房先生在竹简上刻下“四月廿三,入库晚稻三千石,水分三成,可存至明年麦熟”,指节在冰凉的秤杆上轻轻敲了敲:“把西窖的陈麦挪到东窖,腾出位置——后天常州周府的粮船到,得空出十间窖房。”
账房先生的笔尖在松烟墨里蘸了蘸,笔尖的墨滴在账本上洇出个小黑点:“东家,西窖的陈麦是前年收的,已经发了点霉,挪出来怕是要坏。要不……按市价折半卖给粮行?”
“折半?”沈万山掀起地窖的木盖,正午的阳光斜斜切进来,照亮空中浮动的尘粒,“现在把霉麦卖给粮行,不出三日,苏州府就会传遍‘沈家粮囤空了’。你当那些盯着咱们的眼睛,是瞎的?”
他顺着木梯往上走,靴底沾的谷壳簌簌落在梯级上。沈府的粮仓藏在假山背后,从外面看只是片普通的竹林,可掀开竹林下的青石板,十二间地窖能装下三万石粮食——这还只是沈万山在苏州的三处粮仓之一。
刚走到地面,管家沈忠就捧着个铜盆过来,盆里是温水和细布。沈万山净着手,听沈忠报:“刚才漕运衙门的刘师爷来了,说朝廷要加征‘黄河赈灾粮’,苏州府摊了五千石,让咱们这些士族先垫上,说是秋收后由户部补还。”
“补还?”沈万山接过帕子擦手,帕子上绣着暗纹的稻穗,是他特意让绣娘绣的,“至正八年那次‘江淮平乱粮’,户部欠的五千石还没还呢。刘师爷有没有说,这次的粮要什么时候交?”
“说三日内要凑齐,不然就派官差来‘督运’。”沈忠的声音压得很低,“刘师爷还说,要是咱们不乐意,他可以帮忙‘斡旋’——只要送他五百石精米,他就能把沈家的摊派减到三百石。”
沈万山往竹林外走,竹影在他藏青色的绸衫上晃。他想起上月去扬州赴宴,看见丞相之子强夺盐商船队时,扬州的士族没一个敢出声——不是怕丞相,是怕自己的粮囤被盯上。江南士族手里的粮,早就成了元廷眼里的肥肉,只是谁都不愿先被啃一口。
“告诉刘师爷,沈家愿意‘为国分忧’,五千石粮三日内送到。”沈万山在竹林尽头的石桌旁坐下,石桌上摆着刚送来的各地粮价报单,“但得是霉麦——就用西窖那批,让他派人来拉。”
沈忠愣了下:“用霉麦当赈灾粮?要是被查出来……”
“查?谁查?”沈万山拿起报单,指尖点着“汝宁卫粮价:糙米一斗换丝绸半匹”那行字,“河南的军粮都被将领卖到黑市了,谁会管苏州送的是霉麦还是精米?刘师爷拿了咱们的精米,自然会替咱们把账做平。”
他放下报单,看向西边——那里是淮西的方向。三天前,从汝宁卫逃来的一个兵痞,在沈府后门求见,塞给沈忠一块沾血的红布,说红巾军在宿州开了官仓,给百姓分粮。那兵痞还说,汝宁卫的军粮被倒卖,士兵都在往南逃,有的投奔了红巾军,有的成了流民。
“那个从汝宁卫逃来的兵,安置好了?”沈万山问。
“安置在城外的油坊,扮成榨油的帮工。”沈忠答,“他说红巾军里有个少年兵,带着抢来的军粮投奔,现在成了小头目,还说红巾军在招识字的人,给的粮比咱们府里的长工还多。”
沈万山没说话,从袖里摸出个小本子,上面记着他让人打听的消息:河南流民过百万,红巾军在淮西已聚了五万兵,江南漕运的粮船半数被劫,元军在江淮的防线连像样的斥候都派不出来。
“让账房把去年囤积的黄豆清出来,按市价的七成卖给盐城的盐商。”沈万山合上本子,“记住,要让盐商觉得是咱们急着脱手——就说担心朝廷加征,手里不敢留太多粮。”
沈忠有些不解:“黄豆能存到明年,现在低价卖,不是亏了?”
“盐商的消息比漕运衙门灵通十倍。”沈万山望着远处的太湖,湖面波光粼粼,像撒了层碎银,“他们知道咱们在抛粮,就会觉得江南士族对元廷还抱希望,不会急着跟红巾军勾连。可实际上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让盐城的分号,用卖黄豆的银,悄悄收棉布和草药——红巾军缺这些,比缺粮还急。”
正说着,佃户张老栓背着个竹筐过来,筐里是刚收的新茶。他走到石桌前,把茶篓放在地上,膝盖一弯就要跪,被沈万山拦住:“今年的春茶成色不错,按去年的价再加一成算。”
张老栓的手在衣襟上蹭了蹭,黝黑的脸上堆着笑:“多谢东家体恤。俺家那口子说,要是今年能多攒点钱,就给娃请个先生认几个字——听说红巾军那边,认字的人能当小官呢。”
沈万山端起茶盏的手顿了下:“红巾军在你们村传得很凶?”
“可不是嘛。”张老栓蹲在地上,从怀里摸出个粗瓷碗,沈忠给他倒了碗凉茶,“前几日有个逃荒的河南人路过,说红巾军在汝宁卫杀了个李千总,把他私藏的粮都分了。还有人说,红巾军的渠帅是弥勒佛转世,能让地里长出双穗稻——村里有几个年轻人,偷偷收拾了包袱,说要去淮西看看。”
沈万山看着张老栓碗里的茶,茶叶在水里浮浮沉沉。他知道,百姓信红巾军,不是信弥勒佛,是信“分粮”——就像至正六年黄河决口时,百姓信元廷会赈灾,不是信朝廷,是信自己能活下去。可当朝廷的赈灾粮变成密宗寺院的供品,当士兵的粮饷被倒卖给盐商,百姓能抓的,就只剩“红巾军”这根稻草了。
“年轻人要走,拦不住。”沈万山放下茶盏,“但你得告诉他们,淮西现在在打仗,去了未必能活。要是实在想去,让他们路过盐城时,找沈记布庄的王掌柜——就说‘沈先生让来的’,王掌柜会给他们点盘缠,至少能让他们在路上不饿肚子。”
张老栓愣了愣,突然明白过来什么,对着沈万山深深作了个揖:“东家是善人。”
等张老栓走了,沈忠才说:“东家,咱们没必要帮那些要去投奔红巾军的人吧?要是被官府知道……”
“官府现在顾不上这些。”沈万山起身往内院走,“汝宁卫的士兵能带着粮投红巾军,苏州的年轻人凭什么不能?咱们帮他们,不是帮红巾军,是帮自己——要是苏州的年轻人都跑去淮西,秋收时谁来收稻子?”
他走进内院的书房,书架上摆着各种方志,最显眼的是本《元亡策》,是去年从关中老吏的后人手里买来的。书页已经泛黄,上面用朱笔圈着“民无粮则反,士无靠则乱,官无信则亡”。
刚坐下,就见沈忠领着个穿青布短打的人进来,那人低着头,帽檐压得很低。等书房的门关上,他才抬起头——是沈万山派去河南的信使,脸上有道新疤,从眉骨一直划到下巴。
“东家,河南那边……”信使的声音沙哑,“黄泛区的流民推了个叫‘李铁枪’的当渠帅,带着人在黄河渡口抢了元军的粮船。红巾军在宿州开了官仓,分粮时排了三里地的队,连附近的乡绅都偷偷给他们送了牛羊。”
他从怀里掏出块红布,布上用炭写着“盐十引,布百匹,可换淮西通行令”——是红巾军的人让他带给盐商的,他顺手给沈万山带了一份。
“李千总的粮被抢后,元军在河南抓了不少流民抵粮,有个村子因为交不出人,被烧成了白地。”信使往茶杯里倒了半杯冷茶,一口气灌下去,“现在河南的乡绅都在组‘自保团’,有的跟红巾军约了互不侵犯,有的把粮藏进了山洞——谁都不想当第二个被烧的村子。”
沈万山拿起那块红布,布面粗糙,炭字的边缘有些模糊。他想起三年前,元廷还能让江南士族按时交粮;两年前,漕运还能保证半数粮船到大都;可现在,红巾军敢用一块红布当“通行令”,而士族居然要靠囤积粮草才能自保。
“你去歇着吧,伤好之前别再出门。”沈万山把红布折起来,塞进《元亡策》里,“让账房支二十两银子,给你治伤——疤长好了,再去趟淮西。”
信使愣了下:“去淮西?直接跟红巾军接触?”
“不直接接触。”沈万山翻开《元亡策》,找到夹着红布的那页,“去看看他们的粮仓怎么管,士兵怎么练,有没有人懂水利——要是连灌溉都不会,就算占了淮西,明年也得饿肚子。”
信使走后,沈万山坐在窗前,看着院子里的石榴树。去年结的石榴还挂在枝头,干瘪得像个小灯笼。他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:“乱世里的粮草,不是用来吃的,是用来选路的。选对了路,粮草能变成甲胄和人心;选错了路,就是催命符。”
傍晚时,沈忠来报:“漕运衙门的刘师爷让人把霉麦拉走了,还说多谢东家‘识时务’。另外,常州周府派人来说,他们也收到了加征令,想跟咱们合计合计,能不能联合其他士族,少交些。”
“告诉周府,就说沈家已经交了。”沈万山正在看佃户的名册,上面记着各家的人口和田地,“让他们自己拿主意——要是他们敢抗,咱们就偷偷多存些粮;要是他们也交了,就说明江南士族还没到跟元廷撕破脸的时候。”
沈忠刚要走,又被沈万山叫住:“对了,让厨房今晚蒸新麦馒头,给府里的长工和佃户都分两个——就说是‘尝新’,别说是特意给的。”
天黑时,沈万山再次去了地窖。账房先生正在清点新到的糙米,见他进来,忙说:“东家,常州周府的粮船傍晚到了,卸了两千石糯米,说是按咱们之前约的,用糯米换咱们的糙米。”
沈万山走到堆放糯米的地窖前,揭开麻袋的一角——糯米洁白饱满,是做酒的好料。周府是江南最大的酒商,用糯米换糙米,明着是等价交换,实则是想跟沈家结盟:要是元廷倒了,有粮的沈家能保周府的酒坊;要是红巾军败了,有酒坊的周府能帮沈家疏通关系。
“把糯米藏到最里面的地窖,别让任何人知道数量。”沈万山拍了拍账房先生的肩,“记住,从今天起,账上的‘存粮’要比实际少五千石——就当是被虫蛀了,被鼠咬了,总之,不能让外人知道咱们还有这么多粮。”
他走出地窖时,听见远处传来敲更声,“咚——咚——”,是二更了。苏州的夜市应该正热闹,说不定有小贩在卖伪造的赈灾粮票,就像汝宁卫的黑市在卖军粮——这世道,真粮藏在地窖里,假票却在市面上流通,倒像是给这乱世画了幅肖像。
回到书房,沈万山又翻开《元亡策》,借着油灯的光,在空白处写:“至正十一年四月,江南士族囤粮三万石,观河南红巾,望淮西风云,如临渊之鹿,不敢饮,却难离。”
写完,他吹灭油灯,窗外的月光正好照在书页上,那句朱笔圈的“民无粮则反”,在月光下像道未愈合的伤口。他知道,囤积粮草不是长久之计,就像站在河边的鹿,早晚要决定是喝水,还是转身——只是现在,河对岸的红巾军还没露出真正的模样,河这边的元廷却已像块浸了水的朽木,轻轻一推就会散架。
三更时,沈忠突然来敲门,声音里带着急:“东家,盐城分号来信,说红巾军派人去了盐城,想跟盐商买盐,还说可以用粮食换——他们真的有粮!”
沈万山披衣起身,走到窗前。月光下的竹林静悄悄的,只有风吹竹叶的沙沙声。他想起信使说的“红巾军在宿州开官仓”,想起张老栓说的“年轻人要去淮西”,突然觉得,那三万石粮食,或许不用等到秋收,就得派上用场了。
“告诉盐城分号,”沈万山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,“别直接跟红巾军交易,让盐商去谈。咱们只需要知道,红巾军给的粮,是不是新收的糙米——要是连他们都能拿出新米,那元廷的‘赈灾粮’,就真成了笑话。”
沈忠走后,沈万山站在窗前,直到天快亮才回床榻。他没睡,只是闭着眼,脑子里像过走马灯:汝宁卫的士兵倒在粮仓前,红巾军的少年兵带着粮往南走,苏州的佃户在盘算秋收,周府的糯米藏在最深处的地窖……这些碎片拼在一起,像幅还没画完的画,而他手里的笔,正悬在半空,等着一个落笔的理由。
第二天一早,沈万山刚起身,就见张老栓领着个年轻人来,那年轻人背着包袱,脸上带着怯,却睁大眼睛四处看。
“东家,这是俺邻居家的娃,叫狗剩,想去淮西找活路。”张老栓把个布包递给沈万山,里面是两斤新茶,“俺知道不该来麻烦东家,可这娃爹娘去年饿死了,就剩他一个……”
沈万山看着狗剩,那孩子的包袱里露出半截木棍,大概是怕路上遇到劫匪。他想起汝宁卫的赵二狗,想起那个带着红布的少年兵,突然从袖里摸出块玉佩,递给狗剩:“到了盐城,找沈记布庄的王掌柜,把这个给他,他会给你换身新衣裳和盘缠。记住,到了淮西,要是红巾军真给粮吃,就好好待着;要是不给,就回来——苏州的稻田,总需要人插秧。”
狗剩接过玉佩,手一抖,玉佩差点掉在地上。他对着沈万山磕了个响头,声音带着哭腔:“俺要是能活下去,秋收时一定回来帮东家割稻子!”
看着狗剩的背影消失在巷口,沈万山突然觉得,囤积的粮食也好,藏起来的糯米也罢,都不如一个愿意回来割稻子的年轻人金贵。这世道就像片荒田,有的地方在长野草(红巾军),有的地方在枯败(元廷),而他们这些士族,能做的或许不是选边站,而是守住还能长稻子的田,等着那些离开的人,愿意回来。
沈忠走过来,手里拿着刚收到的报单:“东家,淮西的粮价跌了——红巾军真的开仓放粮了。”
沈万山接过报单,上面写着“淮西糙米一斗仅需十文,红巾军辖地百姓可凭户领取”。他笑了笑,把报单折起来,塞进袖里:“让账房再准备五千石糙米,藏到无锡的粮仓——看来,咱们得再多备点粮,说不定过些日子,会有从淮西回来的人,要吃饭呢。”
远处的漕运码头传来船工的号子,沈万山知道,周府的糯米、盐城的棉布、淮西的红巾军,还有苏州的稻田,都在这号子里打着拍子。而他囤积的粮草,就像压在棋盘上的棋子,暂时不动,却已看清了棋局的走向——不是元廷与红巾军的输赢,是这片土地上,总得有人能吃饱饭,能把稻子种下去,能让离开的人,还愿意回来。
小说《逆天命:元清明》试读结束!